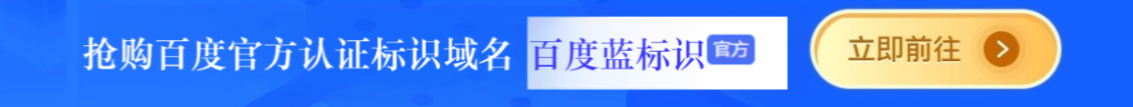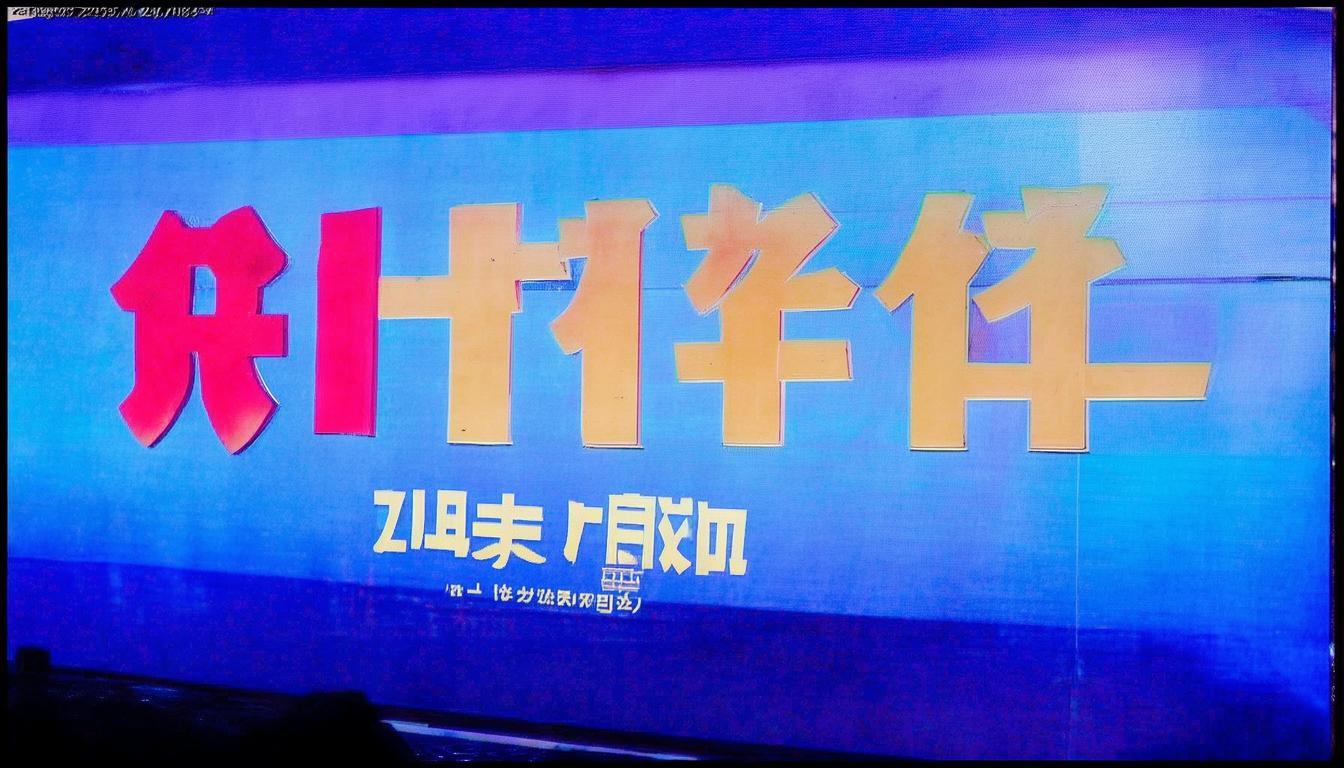在西方世界,古希腊哲学以追求“智慧之爱”著称,这一精神特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较之下,古代中国哲学并非以“爱智”为核心,部分学者提出“成就德行”或“阐明德性”应为我国哲学的显著特征,以此来与西方的“爱智”观念相区别,这些观点均有其合理之处。
若“爱”被视为兴趣,“智”与学术研究相联系,那么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观点特别引人关注,那就是“好学”。必须强调,“好学”并非孔子思想中一个平凡的概念,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好学”构成了孔子思想的核心、根本性的理念。
孔子曾言,即便是在仅有十户人家的村落,也必定能找到一位忠诚守信的人,但他们的好学之心,却不及孔子。
此意表明,具备忠诚守信品质的人并不稀奇,然而真正热爱学习的人却颇为罕见。由此可以推断,孔子将“好学”视为一种尤为难得的品质,尽管在道德传承的脉络中,“好学”未必比“仁爱”或“忠诚”更为崇高(在春秋时期,“忠信”一度是至关重要的德行)。
鲁哀公曾与孔子交谈,提及孔子的门生,孔子回应道:“颜回此君,热爱学习,从不将怒气转移他人,也不犯同样的错误,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如今世上已无此等好学之人。”
孔子门下弟子众多,七十人皆为贤人,然而孔子独独称赞颜回为“好学”,对于颜回之外的其他弟子,孔子则未曾听闻有谁具备此品质。这一事实再次彰显了孔子对“好学”这一品质的重视,以及其难得之处。
深入品味《论语》中的这两段论述,我们便能发现,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置于《论语》开篇,绝非巧合。这正体现了孔子对“学习”以及“热爱学习”的高度重视,其态度之独特,显而易见。
由此可知,孔子所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中的“志于学”并非寻常之意,“志于学”实则是指“好学”的志向。因此,“学”与“好学”不仅构成了孔子思想在学术史上的发端,更是其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关键基石。

那么,究竟何为好学?显然,《论语》开篇便有“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表述,这便是好学者的自我表述。好学首先是将学习视为一种愉悦的体验。明代理学家们提出的“乐学”概念,在孔子的思想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反之,若在学习过程中无法体会到乐趣,那么这样的学习者便不符合孔子对好学者的定义,也不符合孔子所倡导的理想教育。这种责任不仅在于学习者,也在于教育者。
子贡问道:“孔文子为何被尊称为文?”孔子回答:“他聪慧且热爱学习,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为耻,因此被赞誉为文。”
孔文子,即卫国的孔圉,孔子称他为“文子”,原因在于他“聪慧好学,不把向他人请教视为耻辱”,因此,热爱学习不仅是个人享受的乐趣,更是在“提问”与“听闻”的交流互动中得以体现。当然,当时热爱学习的人并非只有颜回,孔子本人也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人,而在孔子的门下,孔文子同样被看作是一位好学之人。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此处阐述的确实涉及多个层面,比如“默而识之”是关于思考,“诲人不倦”是关于教导,而“学而不厌”以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则表达了对学习的无限热爱。这种热爱,与“爱学”“好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孔子说:“我曾整日不吃不睡地思考,却毫无所得,不如去学习。”
《论语》中记录了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言:“每日明了自身所缺,每月牢记所学,这便可以称得上是好学的态度。”时刻明了自身的不足,同时不忘所掌握的知识,正是好学的体现。
孔子留给后人的印象中,“好学”这一特质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这在唐代之前的儒家思想中未曾引起过争议。此特质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当然,这种对民族文化与心理的塑造并非仅限于孔子一人,它与后世儒家学派的演变以及各种社会教育体系的建立同样密不可分。
孔子言:“古时学者修己,今时学者利人。”无论所学何事,其宗旨在于最大限度地提升自我,挖掘自身潜能,非为向他人炫耀。学习旨在自我受益与愉悦,此等受益与愉悦,乃追求心灵幸福者所追求的精神与心智之满足。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孔子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