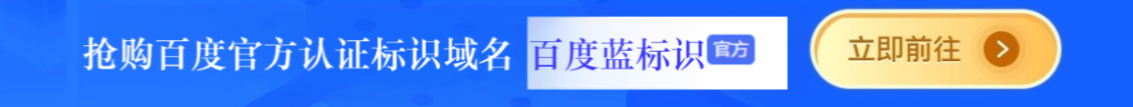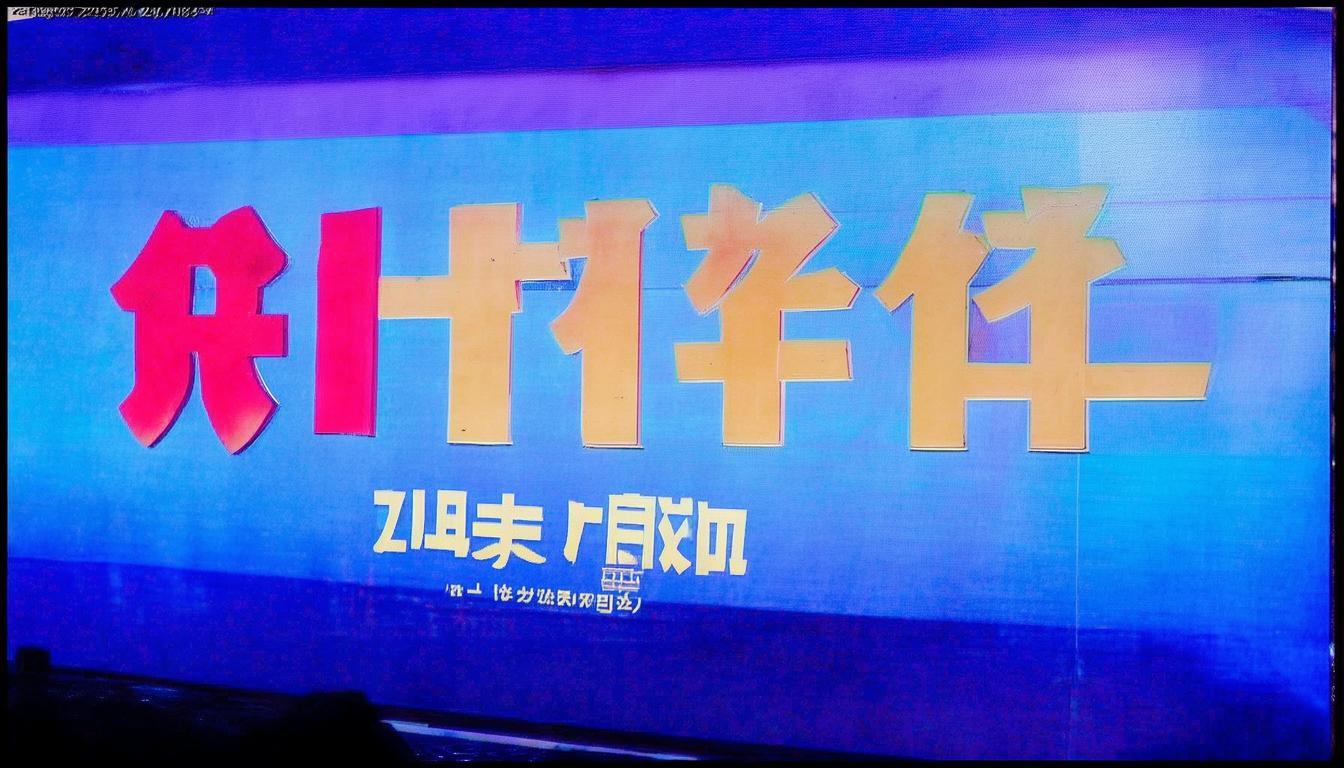今年正值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的私家历史栏目携手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共同策划了“抗战回望”专题系列。该系列通过选取抗战时期的报纸、图书、日记等珍贵史料进行详细介绍,旨在引领读者深入历史现场,感受那个时期中国军民的英勇精神与日常生活。
本文对《江苏省江南两年来政情述要(民国二十八年一月至二十九年十二月)》进行了介绍,该书详细记录了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在敌后进行的抗战活动及其行政措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国民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设立了“省政府行署”。起初,这些行署是由各省省政府自行创建,并配备了类似性质的机构。随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了《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通则》,正式明确了行署的合法地位——各省先前设立的类似行署组织均按照规定进行了改组,并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同时,其他省份也纷纷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在适宜的地区设立行署。该规定明确指出,行署的设立旨在“提升地方行政管理效率,以适应战区实际情况”,在权力范围上,行署负责在其管辖区域内代表省政府行使职权,当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发文时,则由行署主任进行副署。
江南行署下辖各县及其分类(1940)
陈之迈在谈及行署的设立时提到,抗战时期,敌军入侵,导致一些省份因战事影响而出现分裂,交通受阻,省政府难以对全省范围内的各县进行有效监督和指挥。尤其是沿江省份,情况更为严重,因为敌人暂时控制了长江,这些省份的部分地区位于江南,另一部分则在江北,指挥调度极为不便。江南行署无疑是陈之迈论述的最佳例证。
《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条例》(1944)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国民政府选择西移,与此同时,江苏省政府及其下属的各厅、处则选择向北方迁移至淮阴。到了1938年7月,顾祝同,当时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并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在安徽省设立了江苏省政府江南办事处。由于江苏省政府江南办事处的辖区有限,难以广泛实施,故在1939年元旦,设立了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该行署是在行政院颁布设立省政府行署的相关法令之前自行设立的),由时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的冷欣担任主任。
冷欣对江南行署的概况进行了描述,他指出:“江南地区的环境极为艰苦,当地情况复杂,推行政务的难度在全国各游击区域中堪称首屈一指。”江南行署管辖着二十六个县,其范围从东边的上海延伸至西边的古都南京,重要的城镇和交通线路大多被敌伪势力所控制,而在我方军力控制下的整个县境,唯有溧阳一县。
《修正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组织暂行规程》明确指出,江苏省政府设立江南行署,旨在抗战时期便于就近处理江南地区的各项政务。该行署下辖区域包括所有江南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区保安司令部、各县政府以及地方团队,还有直接隶属于省政府或各厅、处的机构。在行署的管辖范围内,以江苏省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其性质与国民政府设立的行署并无本质区别。江南行署驻地位于安徽屯溪。
《江苏省江南两年来政情述要(民国二十八年一月至二十九年十二月)》一册于1941年问世,其书名由冷欣亲自题写。在封面的左上角,清晰可见“机密”二字。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作者和出版社并未在封面上标注,这表明它是一部仅供内部阅读的出版物。全书涵盖了县级行政管理、民族自治、保甲制度、动员与训练、粮食储备、烟草禁种、救济事业、抚恤与表彰、锄奸行动、税收征收、省县两级预算、会计与金库管理、地方金融体系、地方教育行政管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教育经费筹集、编审工作、经济斗争、粮食统制、生产提升、农业贷款发放、合作事业发展、交通与通讯、水利设施建设、地方武装力量等多个方面,内容丰富,无所不包。以下内容将对该部分进行简要阐述,重点涉及江南行署的行政管理以及抗日斗争的相关事宜。
《江苏省江南各区县常备队战时短期教育起居日课时间表》
江南行署的施政环境相当复杂,冷欣在序言中明确指出:“治理国家并不困难,但在战争时期治理则尤为艰难,而在战争爆发前治理则更为困难。”具体来说,这种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敌人与伪军频繁侵扰,导致周围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原先的策划无法得以从容实施。
二、据点密布,交通梗阻,政情之下传上达,悉多所扞格。
三、兵燹以后,典章册籍,散失殆尽,兴废继绝,无轨范可循。
四、奸邪之徒与非法团体,凭借谎言肆无忌惮地煽动人心,导致民众的纯朴本性逐渐丧失,若是宽容,则可能陷入玩世不恭、犹豫不决的境地,若是严厉,则恐怕会引发如同驱赶鱼雀般的担忧。
五、地方贤达,作避秦计,多流亡异地,各级机构,致叹才难。
农村与市镇遭受了轰炸、焚毁和劫掠,经济陷入了崩溃,财源枯竭,政府经费也变得紧张不足。
江南行署在经过一年的努力建设之后,其各项政务虽已初具规模,但仍旧未能步入正规轨道。这一点,正如冷欣所坦承的,在后续的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1939年,为了便于行政管理,江南行署对其所辖各区设立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时,各县县政府也相应地设置了行署。这些行署分别承担了原本由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各县县政府行使的行政职权。1940年1月,江苏省政府出台了《江苏省战时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置办事处办法》和《江苏省战时各县县政府设置办事处办法》。因此,之前设立的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行署被撤销,并重新设立了办事处。这一举措旨在配合行政院对行署进行合法化和正式化的处理,也就是为了避免行署之间出现混淆。
《各县受训人员籍贯及人数统计表》

在江南行署的保甲工作中,首要任务是修改保甲章程。这是因为之前的保甲章程在战前适用,但在战时却显得格格不入。战时的情况与平时大相径庭,适用于平时的措施往往不适用于战时。平时举办保甲,旨在稳定社会秩序和增强自卫能力,而战时举办保甲,则应侧重于组织民众、凝聚力量、统一意志以及协同抵抗敌人。
修订的细节颇多,其中两点尤为引人关注:首先,对“联保连坐切结”进行了修正——“由过去的联保连坐切结,限定连坐对象为那些与‘匪’有勾结的,现在为防范奸细活动,在切结条款中新增了勾结汉奸这一项,若联保户中有发现勾结汉奸的情况,所有联保户都将受到连坐惩罚;其次,原先规定联保户不得少于五户,现调整为同甲联保,旨在整顿秩序”。
二、对保甲规约进行修订——“原先的保甲规约内容主要侧重于自治和自卫相关事宜,如今为了适应军事需求,在新的规约中加入了侦查汉奸和敌对间谍的活动、禁止销售敌国货物和流通假币、优待军人家庭、破坏敌方铁路、公路、电线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的内容,同时提倡国民兵役和工役制度,以及救护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工作”。
这两项调整显然是为了应对战时需求,然而,具体能实施到何种程度,实难预料。特别是在那些形势错综复杂、敌我双方武装力量交织的地区,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即便是在不得不接受,甚至支持“两面政权”的情况下,江南行署所规定的严格保甲制度,其真正执行到位的程度,也显而易见。
《忠烈事迹调查表》
江南行署在策反领域出台了《策动伪组织反正办法》共九项条款,以及《伪组织人员反正奖励办法》五项条款,将这项工作细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即外部的策动工作和内部的潜入策动。外层策略包括编制印刷材料,传播中央对既往德行的宽恕以及对归顺者的奖赏信息,将这些材料分发给所有附逆人员,以期他们能彻底悔改。同时,对于参与伪组织人员的亲友,弘扬抗战精神,阐述附逆的弊端,唤起他们的良知,促使他们从旁协助。至于附逆人员的直系亲属,则鼓励他们迁往我军控制区,并提供优待,以此吸引他们归顺。这一策略,中共亦十分熟悉。
在潜入策动这一领域,该书可能考虑到保密要求,未能将其详细内容公之于众,因而有所简略。至于策反工作的实际成效,书中仅提及“过去一年中,有相当数量的敌方人员选择反正,但具体姓名则未予透露”,这同样是为了维护保密原则。
《江苏省江南各县二年来锄除奸伪调查表》
在税收问题上,该著作对整治田赋、契约税以及其他各类税收进行了详细阐述。鉴于对田赋的整治最能体现江南行署在当地的治理状况和积极进取的态度,本文将重点介绍其中的田赋内容。在江南行署的管辖范围内,自沦陷以来,已有三年未征收田赋,同时,原有的土地登记簿籍也遭受了较大损失。江南行署据此出台了《各县田赋册串暂行保管办法》,并要求其管辖范围内的各个县务必对田赋册串进行细致的整理与妥善的保管。
随后,随着国民革命军陆续收复宜兴、溧阳以及高淳三地,这些地区的部分游击部队也逐步恢复了活动。相应地,在行政职能得以恢复之后,各个县份的经费支出也随之持续上升。是以,江南行署以“江南连年丰收,连续三年减免赋税,民众负担已有所缓解”为依据,自1940年起恢复征收宜兴、溧阳和高淳三县1939年的田赋,而1940年这三县的田赋则暂缓征收;青浦、松江、金山、南汇、奉贤、川沙、上海、宝山、嘉定等九个县因“环境特殊,无法启动征税”,这显然是由于日军控制严格;至于溧水、金坛、江宁、丹阳、句容、江阴、武进、吴江、吴县、无锡、常熟、昆山、太仓等县,则依照193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的《战区土地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救济暂行办法》中规定的“沦陷地区经过收复,或为我游击部队控制并行使政权之区域”的土地赋税与附加税“应予减免,原则上不超过原税额的百分之五十”,实际征收这些县份的田赋为原税额的五成。
《战区土地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救济暂行办法》
观察之下,江南行署实际上是在法律规定的最高额度内对那十几个县征收赋税。然而,新近收复且持续在敌对双方争夺中的宜兴、溧阳和高淳三县,却按照原有田赋的全部金额进行征税,这或许并不完全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江南行署在执行法律时,对规定有着相当程度的灵活处理,这种处理在特定情境下或许可以理解,然而,对于那些时常需向多个政治势力缴纳田赋、且历经战乱之苦的当地民众而言,这无疑又增添了一份沉重的负担。
正因如此,江南行署此项措施能否真正得以实施,再次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回顾1940年江南行署的预算,预计可从这些县份收取田赋共计七十万元。然而,最终的情况是,镇江、丹阳、江宁、句容等县因原有田赋册籍全部遗失,再加上敌伪势力频繁袭扰,征收工作极为艰难,很多地方都不得不中途放弃。唯有宜兴、溧阳、高淳、金坛、溧水这几个县份能够顺利完成征收任务,最终全年实际征收的田赋达到了五十余万元。
全书内容详述了江南行署的治理过程,然而在叙述中,部分内容表述不够清晰,有时甚至省略了某些事实、人名、地名或数字,这或许是为了保密而有意为之,尚可接受;然而,另一方面,书中频繁探讨江南行署的制度设计和规划,却未能向读者揭示这些措施是否真正实施,成效如何,这两方面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书的参考价值。
然而,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两个不足之处实际上揭示了江南行署在当地的治理成果,至少在本书面世于1941年之前,其治理效果相当有限;其治理成果主要集中在国民政府军队主要掌控的数个县区,否则图表与文字说明中不会出现如此多的空白。正因为江南行署的治理成效并不显著,所以现今所能查阅到的相关历史资料相较于其他敌后区域更为稀少,因而这本书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突显。
《江苏省江南各区县常备队战时短期教育全期学术科时间配当表》
编撰该书之际,江南行署所辖区域日军兵力骤增,汪伪政权亦加强清乡措施,使得江南行署的处境愈发岌岌可危。毕竟,尽管江南行署及其下属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府与县政府竭尽全力,但若无武力作为后盾,终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理,与行政部分内容相对而言,书中对地方武装的吸纳、构建、训练以及战果的描述更为详尽,同时也揭示了江南行署在行政成效上的不足之处。
《江苏省江南各区县常备队战时短期教育术科基准表》
回到起点,冷欣在序言中提及的“治理国家并不困难”这一观点,显然仅是他个人的见解。若非如此,那么为何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十年间,众多地方的行政状况普遍恶化?更有观点认为,担任县长需具备三个“万”的才能,即“万死不辞”、“万恶不惧”、“万能在手”,这难道不是徒劳无功之举吗?鉴于他在战争爆发前并未真正参与过地方行政管理工作,且始终在军队中服役,这种地方行政经验的缺乏或许正是导致他形象固化的原因所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方行政管理多围绕军队需求展开,前线及敌后地区的政权往往离不开军队的支持,众多像冷欣这样的军人,此前并无地方治理经验,却得以执掌一方政务,他们或许也存有冷欣那样的成见。对于军人涉足政治,后世评价各异,战时便已有不少质疑之声,而要求“军政分离”的呼声日益强烈。关于军人涉足政坛的现象,本文暂不发表任何观点,然而,期望通过剖析军人从政这一特定事例,能为对该现象的评估提供若干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