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蔫哏宗师”走了
7月9日下午,94岁的在天津去世。
当天黄昏时分,相声艺人苗阜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了杨少华离世的消息。苗阜透露,他上一次与杨少华见面是在好几年前,那是在央视举办的《春晚倒计时》节目中,当时杨少华的身体状况还算良好。
尽管在20世纪中期,杨少华曾为马三立和马志明父子担任捧哏,然而观众对于90年代之后的杨少华形象似乎更为熟知。
在那个时期,他先后与赵伟州、杨议携手演出的《枯木逢春》、《肉烂在锅里》等相声作品,赢得了众多相声爱好者的喜爱。
李文华先生离世之后,杨少华先生也受到了一些相声迷的赞誉,被称作是那位传承“蔫哏”相声艺术的最后一位演员。
著名相声演员杨少华 图/天津市曲艺团
因不认字差点丢了师父
杨少华,这位北京出生的人,多次在多个场合讲述过自己的童年往事。在他眼中,那段贫困潦倒和充满挑战的时光,实在难以引起怀念之情。
他曾向《天津日报》表示:“过往的种种,我很少愿意去回忆,那些记忆总是让人感到心烦。住在狭小的屋子里,娶了一位妻子,然后接连生了这么多男孩。老实说,每当想起这些,心中都充满了痛苦。”
杨少华未曾料到,那些接连出生的男儿,在他晚年时,竟会给他带来更多的痛苦,这自然是后来的事情了。
杨少华回忆起童年,家中颇为贫困,仅有一间小屋,空间狭小,哥哥常常外出,不知去向,自己便主要由姐姐照料长大。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位于北京西单地区的启明茶社享有相声界“黄埔军校”的美誉,汇聚了众多相声界的佼佼者。这里,经常有张寿臣、赵霭如、刘德智、吉坪三、华子元、于俊波、侯一尘、郭荣起、王世臣、刘宝瑞等相声大师登台献艺。
幼年时的杨少华因无所事事,曾先后潜入启明茶社与明园茶社,最终得以担任一个名为“检场”的职务。所谓“检场”,实则是指杂役,负责在演员更换节目时上台摆放鼓具,待演出结束后再将它们撤下。而当角落的演员表演完毕,便摇响铃铛,以此宣告演出结束。
在打扫卫生之际,杨少华偶得顾客遗失的零钱,脚下沾了糖果,一踏便粘在鞋底,此事传至演员群体,杨少华因而遭受责罚,头部肿起大包。
在那个时期,园子里的老先生时不时地给杨少华传授一些相声片段,实际上传授的不过是寥寥数语,而更多的是通过园子特有的氛围“熏陶”,通过多听多看,杨少华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了其中的韵味。
杨少华回忆起过去,提及自己获得《报菜名》的文稿时,却发现一个字也不识,于是只得求助于识字的孩童,以糖果作为交换,请他们为自己朗读。
由于不识字,差点就错过了拜师的良机。在园子里,杨少华与常宝霆(艺名“三蘑菇”)年纪相仿,两人关系尤为亲密。在常连安父亲的推荐下,常宝霆得以成为相声艺人郭荣起的徒弟,杨少华也因此心生向往,渴望能成为郭荣起的徒弟。
郭荣起询问杨少华:“你是否懂得阅读?能否为我朗读报纸上的广告内容。”杨少华回应道:“既然你自己都不识得字,我又怎能知晓?”郭荣起接着追问:“那么,你能否骑自行车?”杨少华回答:“我并不擅长骑自行车。”
郭荣起瞧见那孩子一无所长,顿时显得很不悦。尽管如此,在常宝霆等人的多次撮合之下,杨少华最终还是将郭荣起视为自己的师傅。
在杨少华的记忆里,郭荣起并未向他传授过多技艺,倒是与他一同长大的常宝霆,时常向他传授技艺。
在杨少华的记忆中,直至他重返天津的前夕,师父未曾向他传授过任何技艺。起初,他在园中劳作,所有技能都是通过耳濡目染自学而来。他边听边学,边听边记,这样的学习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潜移默化的熏陶。
阴差阳错又说了相声
杨少华在十九岁那年,由于姐姐的婚事,他随姐姐一同迁往天津,原本以为此生与相声无缘。
姐姐远嫁至天津,在一家钢铁厂找到了工作,杨少华亦随姐姐的脚步,在工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起初是在建筑工地,之后转至工厂,杨少华在工厂从事装卸工作,之后又担任了钳工,这一干便持续了数年之久。
实在未曾预料,到了1949年,启明茶社宣布停业,众多曾在启明茶社活跃的相声表演者纷纷涌向天津寻求生计,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迁回天津的相声名家常宝霆及其家人。
童年的挚友竟在天津意外重逢,这情景让杨少华欣喜不已。他们日复一日地谈笑风生,沉迷于麻将的乐趣,玩得不亦乐乎。常宝霆找到杨少华,诚挚地邀请他继续投身相声表演,不要就此放弃。
杨少华原本打算放手,然而面对常宝霆的耐心劝说和缠绵不舍,他最终还是决定重新拾起相声。起初,他在工厂中表演,不久便成为了厂内文艺活动的中坚力量。随后,朋友们纷纷加入,他们一同前往天津的相声园子进行业余演出,也因此赢得了众多专业相声演员的青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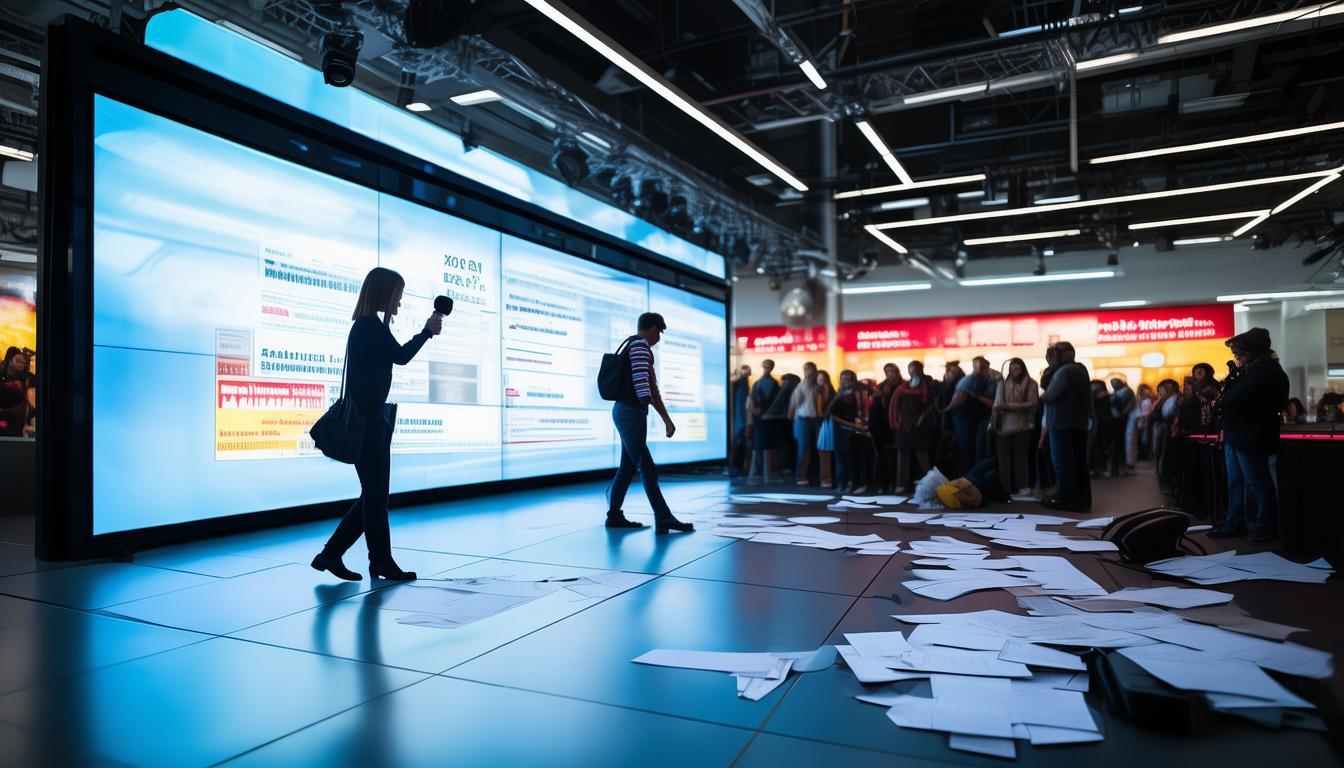
杨少华曾有所忆,他曾造访南开区的相声团队,与队员们嬉笑打趣:“若我能表演一段你们都熟悉的相声,我便从此不再涉足相声界。”未曾想,一番表演后,队员们竟对他刮目相看。于是,杨少华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工厂的职务,立志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相声表演者。
在20世纪60年代的开端,为了保障基本生活,杨少华在天津的多个公园,如人民公园和水上公园等地,开始了相声的演出生涯,期间有幸与相声界的泰斗马三立共同登台献艺。随后,他被分配到了天津市曲艺团工作。进入70年代,杨少华开始担任马三立之子马志明的搭档,为其捧哏。
杨少华与马志明携手不久,便因性格差异及艺术风格上的分歧等多种因素,共同宣布了终止合作的决定。关于具体原因,各方说法不一,然而时至今日,仍未有明确的结论得以公布。
相声艺术的历史长河中,捧与逗演员因种种缘由而分离的情况并不罕见,尽管业内流传着各种离奇的传闻,但作为相声的爱好者,我们只能感慨一声“实在遗憾”。
实际上,在告别了马家两代杰出的相声表演者之后,90年代,杨少华终于迎来了个人艺术的巅峰时期,而他的“蔫哏”式艺术风格也在此期间逐渐稳固成型。尽管给人感觉反应略显迟钝,但杨少华却经常能够巧妙地抛出令人惊叹的笑料,效果出奇地好。
杨少华觅得了一位在艺术上与他极为契合的伙伴,这位天津人氏的相声演员,被相声迷们昵称为“狗神”的赵伟州。在相声领域,“狗”并非贬义,反倒是其生动鲜明的个性,颇得众多相声爱好者的青睐。当“狗神”赵伟州与“蔫哏”杨少华相遇,两人瞬间在艺术上擦出了绚烂的火花。
赵伟州不仅与众不同,与其他捧哏演员相比,他深知杨少华的艺术特色,在创作过程中更愿意让杨少华彰显个人风格,且并不觉得捧哏演员会抢占自己的风采。
赵伟州(左)杨少华(右)同台表演 图/视频截图
在此背景下,新创作的相声《枯木开花》得以完成,而作品里那句“我要开花”更是使得杨少华凭借电视和广播的传播,在全国范围内被众多相声爱好者所熟知。
遗憾的是,杨少华与赵伟州的合作并未持续长久,进入21世纪,他们终止了合作。此后,杨少华选择站在自己最小的儿子杨议身旁,全心全意地支持他在相声舞台上发展。
在杨少华的晚年,几乎所有的高光和争议,都和小儿子杨议有关。
再无蔫哏?
在不少观众看来,站在儿子身边的杨少华比之前更“蔫”了。
杨少华曾提及,与儿子共同登台表演相声,其难度颇高。在同行之间,相互间可以占些便宜,但在父子这一特殊关系中,这种做法却不再适用。加之年龄差异,儿子创作的新段子,自己往往难以跟上,常常是记不住台词。有时,上台前只能将词句抄在掌心,然而,演出前若去洗手间洗手,回来一看,掌心中的词句却已消失无踪。
杨少华(右)和儿子杨议同台演出 图/中新社 苏振强摄
尽管如此,在2003年举办的央视第二届相声大赛中,这对父子凭借他们的新作品《肉烂在锅里》荣获了一等奖。在那个时期,观众们对于相声的新作品充满了期待,并且展现出极大的宽容度。
在荣获奖项的第二年,杨议亲自执导并出演了都市喜剧《杨光的快乐生活》,该系列共拍摄了九部。在剧中,杨少华扮演了杨光的父亲杨丰年,忠实地展现了角色的性格。由于这部电视剧的热播,父子二人的知名度得到了显著提升,杨少华的名字也因此变得更加响亮。
之后,杨少华及其子杨议多次尝试冲击春晚舞台,却屡遭挫折。然而,直至2018年,他们才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亮相央视春晚。不过,他们表演的并非相声,而是一部名为《为您服务》的小品。
那一年,杨少华年届八十六。相声的版图悄然发生了转变,曾经盛行于电视台的相声艺术,如今又重返了剧场。那些曾与他同台献艺的伙伴,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则成为了相声界的泰斗。而他自己,身体条件也不再允许他频繁登台。在市场上,“蔫哏”的表演风格也逐渐被更加热烈的表演形式所替代。
近些年,杨议屡次深陷相声界的争议漩涡,而年纪已高的杨少华,既无法加入其中,也无力对局势产生任何影响。
有人在杨少华去世后,称他为“蔫哏”创始人。
实际上,“蔫哏”这一艺术流派并非他首创,在杨少华赢得观众喜爱之前,相声界中姜昆的黄金搭档李文华,就已经是“蔫哏”风格的佼佼者。机智的相声表演者总是能依据自身的特色,探索最契合自己的表演风格,而非盲目地追求对传统的简单模仿。杨少华并非首位以“蔫”著称的相声艺人,同样地,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位。
杨少华这个名字,在岁月的流转中早已成为了一个象征,承载着丰富的内涵:他是被誉为“相声活化石”的代表性人物,是一位亲历并见证了相声界兴衰变迁的长者,同时也是相声演员杨议的父亲……
他生前遗留的纷争,在他离世后,将逐渐淡去。若干年过去,那些尘封的往事或许会被人们遗忘,然而,那个眼袋几乎垂至地面的干瘪老头,以及他嘶哑地喊出的那句:“我要开花”,或许还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对于杨少华来说,已经足够美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