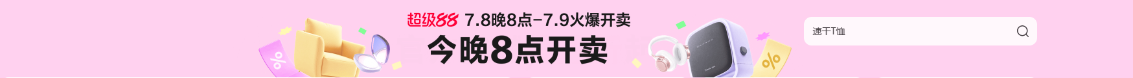董子健、周冬雨、五条人、papi酱、黄渤、大鹏、白客、彭磊、贾樟柯、王红卫、许知远、王宏伟、毕赣、蔡康永……究竟哪部影片能够将如此众多来自不同行业的大咖汇聚一堂?
非商业巨作,非名导照耀,却是一部极具艺术特色的动画影片——《艺术学院1994》。
《艺术学院 1994》海报
杨城担任制片人,刘健执导此片,影片描绘了1994年南方某艺术学院内一群美术生与音乐生在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所经历的种种事件。该片曾入选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金熊奖”提名,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登上了世界电影艺术的顶峰。
观察整体画面,随着动画逐渐趋向于真人电影的风貌,该片以一种近乎固执的纯粹态度,运用最“原始”的手绘手法,向艺术和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致敬。
其不仅因其手绘效果的独特美感而备受瞩目,而且通过对90年代青年艺术追求的细致刻画,使得观众得以重返那个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30年前时代。
《艺术学院 1994》的制作人杨城、导演刘健以及配音演员仁科,依次出现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现场(从左至右排列)。
近期,极客电影(ID:Geekimovie)对制片人杨城进行了独家专访,他向我们娓娓道来电影的创作历程,同时分享了自己对艺术电影独到的见解和对未来的憧憬。
制片人杨城
作为电影的制片人,杨城始终站在艺术与现实的交汇点上。
他全面投入了这部影片从剧本创作到画面绘制、声音录制,直至最终上映的整个制作过程,目睹了导演刘健以近乎孤军奋战的手绘风格坚持不懈,同时凭借其在艺术电影领域多年的积累,努力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探寻突破的路径。
《艺术学院 1994》一部现实主义手绘二维动画电影
艺术究竟是什么?
在这次对话里,杨城并未借助宏大的理论框架来对艺术进行界定,或许正是因为艺术的这种“难以界定”的特性,才使得它散发出最为纯粹和动人的光芒。
他并未躲避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反而于疫情持续的三年里,在停工与恢复生产、手绘动画的漫长制作与执着坚持中,彰显了一位艺术电影工作者的坚韧精神。
他不仅坦率地揭示了艺术电影在现今所面临的生存挑战,而且对中国电影的“多样性”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郝丽丽(配音演员为周冬雨)与高红(配音演员为Papi)的形象,由黑白线条勾勒而成,两人并排坐在飞机模型之上。她们面朝镜头,嘴角上扬,流露出自信的微笑。即便只是画面,也能明显感受到她们对遥远天际的憧憬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在访谈过程中,杨城谈到了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带来的影响,他坚信,只有当艺术家们拥有AI技术无法取代的独特技能,AI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用。
或许,他们就像《艺术学院 1994》里那些在困惑中激情蓬勃成长的青年,这恰好与杨城以及他投入其中的事业相契合。
在艺术追求的无限自由与实际条件的限制之间,他始终不懈地探索着中国艺术电影的发展潜力。
01 艺术的温度:理想主义从未过时
在杨城眼中,操盘一个电影项目始终是一门关于“关系”的艺术。
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事与事的关系,都包含在内。
通常来说,若将影视作品类比为建筑物,导演便等同于建筑设计师,而制片人则扮演着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掌控者角色。
导演担负着绘制艺术构想的职责,与此同时,制片人需在现实环境中调配资源、掌握进度,确保梦想得以变为现实。
这种在艺术表达与商业策略之间寻求平衡的思维方式,始终贯穿于他与导演刘健的整个合作过程。
导演刘健(左)、制片人杨城(右)
《艺术学院1994》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起源于导演刘健在重返母校时所受到的强烈感动。
三十年前,那些充满活力的教师如今已是满头白发,校园的景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对时间流逝所引发的复杂情感,正是影片创作的最初动力。
《艺术学院 1994》引领你领略1994年文艺青年们的精神风貌。
杨城回忆道:
导演漫步在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之中,猛然感悟到时光的无情以及青春的多重滋味。
这种源于生活体验的创造欲望,使得电影不再仅仅局限于怀旧,而是转变为对艺术和青春不朽探索的深刻思考。
同时1994年对于电影史来说,也是一个充满纪念意义的年份。
《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低俗小说》、《活着》等众多在各大电影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高分影片,均诞生于同一年份。
因此,无论是艺术追求的理想,抑或是电影艺术本身,1994年都堪称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
在杨城的观点中,艺术电影的价值核心在于其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尽管故事背景被设定在1994年,但角色们对艺术的热爱、对未来的困惑,却与现时代每一个细腻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这种对普世情感的关注,正是杨城选择参与这部作品的核心原因。
特别要提的是,本作的结尾曲目采用了崔健的《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崔健于1991年推出的著名专辑《解决》里,完美地诠释了那个既充满理想又充满迷茫的时代精神。
整首歌曲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种狂野的“狂躁”气息,其编曲既新颖又充满动感,更蕴含着最真挚的纯真情感,恰好与电影中那些艺术青年们的焦虑与不安形成了完美的呼应。
02 坚持手绘:五年磨一剑的创作旅程
《艺术学院1994》的制作历程被誉为一番“动画的征途”。导演刘健执着于纯手工绘制的创作手法,并率领中国美术学院师生队伍,历经五载时光,最终圆满完成了这部作品。
《艺术学院 1994》纯手绘创作,历时五年才完成
翻看导演的履历,“手绘”一直是他的个人标签。
自《刺痛我》问世之初,历经2017年《大世界》亦入选柏林电影节主竞赛环节,直至现在《艺术学院1994》的上映,刘健导演的执导手法始终如一,作品质量亦保持恒定。
《刺痛我》、《大世界》以及《艺术学院 1994》这三部作品,全部都是采用纯手工绘制的艺术形式创作而成。
杨城坦言,这种选择在商业动画盛行的当下极具挑战性:
手工绘制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代价和人力资源,然而刘健导演坚信,唯有这种饱含情感的笔触,方能传达出他追求的质感。
在创作的起步阶段,团队遭遇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确保风格的统一。刘健对画面质量的要求极高,以至于连线条的弯曲程度都需经过多次琢磨。
为了实现“众人齐心,共绘一画”的理想效果,该团队投入了半年的时光进行深度协作,对色彩搭配、人物动作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反复的微调与优化。
《艺术学院 1994》风格独特
杨城回忆道:

在那段时间里,整个工作室宛如一部精密运作的机械,每个人均致力于追求那个一致的美学理想。
疫情的突然爆发加剧了原本就严峻的制作困境。原定三年内完成的项目,不得不延期至五年才能完成。
在资金短缺的困境中,杨城作为制片人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四处奔波,积极寻求各方援助。与此同时,整个剧组也似乎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这部电影值得他们竭尽全力去完成。
面对重重困难,刘健导演并未因外界因素而降低影片的硬件质量标准,反而在逆境中奋勇前行,持续提升品质标准,力求制作水平更上一层楼。
对艺术的极致探求,最终塑造了该电影独有的审美风格,不仅保留了传统国画的意境韵味,还巧妙地融合了现代艺术的创新精神。
《艺术学院 1994》兼具写意风与写实风
在声音创作的领域,制片人杨城与导演刘健勇于打破常规的配音方式,他们广邀来自各行各业的有才华人士共同参与“声音演出”,这不仅展现了艺术的宽广自由度、深厚包容度以及多元丰富性。
天台“整活”剪头
尽管网络对这批全明星配音演员的配置评价各有千秋,杨城却坚信,这一选择并非只是注重表面形式,实则更贴合电影的核心需求。
杨城说道:
初观此片画面,我即刻领悟到,它实际上描绘了一个时代的众生相,其中讲述了一群年轻艺术家在人生抉择关头的经历。
因此,在挑选配音演员阵容的过程中,我们同样期望展现出一种集体形象的氛围,而非仅仅依赖单一的声音特色。
自然就想到邀请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共同参与,会比较有意思。
男厕所东倒西歪的艺术生,这是真“上头”
另外,杨城还认为,本片与一般的动画电影不同。
在一般的动画影片里,配音的角色多为小动物、各种物品,亦或是具备特异功能的个体,然而在本部影片中,出演者却全都是来自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通人。
而且本片在人物塑造上比较有个性,情感表达也比较细腻。
因此,在挑选某些角色时,必须依赖具有专业素养的演员,他们通过自身的表演和独特的嗓音特点来刻画角色形象,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配音工作。
因此,杨城与导演共同确立了这个创作方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来挑选恰当的人才,并成功邀请他们加入创作团队。最终呈现出的成果,确实让人感到十分惊喜。
路边排排坐喝牛奶,极具松弛感
谈及如何促使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们齐心协力为电影配音,杨城在回答时不禁流露出几分自豪之情:
刘健导演本身具备一定的导演功底,他之前执导的电影《大世界》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此外,我们在该领域结识了众多好友,其中不少配音艺术家与我们直接相识,而其他一些人则可通过朋友关系取得联系。
在疫情期间,我国电影产业遭遇重重挑战,然而,众人齐心协力,越发紧密团结,因此,邀请他们加入这一活动并未耗费过多精力。
疫情使得众人出行受限,加之联系对象众多,因此整个项目历时近半年方才圆满结束。
03 寄语未来:夹缝中依然有艺术的火种
杨城,一位在艺术电影领域耕耘多年的制片人,对行业现状保持着敏锐的洞察。
他坦言,艺术电影的生存环境依然严峻:
市场上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类型明确、节奏紧凑、刺激强烈的商业影片,而艺术电影则常常遭遇排片量不足、观众认知度较低的难题。
但他并不因此气馁,反而从柏林电影节等国际平台看到希望:
在柏林举行放映的《艺术学院1994》影片,吸引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他们均被其故事所触动,这充分展示了艺术电影普遍的价值所在。
在杨城的视角中,艺术电影所承载的行业价值在于其能够“开辟出新的可能性”。
它在艺术语言的运用和风格形式上不断寻求创新,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洞察时代、洞察世界、洞察人性的全新视角。
他特别指出,《艺术学院1994》这部作品对90年代艺术生态的描绘,不仅是对过往的缅怀,同时也为现时的艺术教育提供了借鉴:艺术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艺术与时代、与个人的联系又是怎样的?
小桥上谈论“人生理想”的文艺青年
谈及艺术电影的未来,杨城提出两点展望:
我们热切期盼,在国产电影暂时的低潮期,能够孕育出更加兴盛与健全的电影文化,届时观众对电影的探讨与交流将拥有更加真挚、坦率、宽容的气氛,这将成为艺术电影赖以生存的沃土。
我们同样期盼全球优秀的艺术影片能在中国有更广泛的上映机会,如此一来,才能有效培育并稳固扩大艺术电影观众的基础。
草坪“躺平”惬意又自在
他还谈到了最近大火的AI创作,他认为:
如果创作者本身不够强大,那么你最终也很难把工具使用好。
只有当创作者本身具备很高的能力,才能让工具发挥更大的价值。
否则,随着工具的广泛应用以及技术难度的降低,每个人都将能够借助这些工具轻松完成基础的操作。
以往众人或许都是从零基础起步,然而如今,随着创作工具的广泛使用和技术难度的降低,众人的起始水平普遍提升至了60分。
这便意味着你需展现出远超60分的创新实力,方能于激烈的竞争中独树一帜。
在本次访谈接近尾声之际,杨城满怀深情地祝愿那些依然执着于艺术创作的年轻艺术家们:
尽管我认为年轻艺术家常常会感到不安,然而,身为艺术家,他们实际上能更有效地应对这种不安,因为这是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它还能使他们保持警觉,避免陷入惰性。
因此,对于如此美妙的艺术,我们仍旧应当沉浸于其创作过程的乐趣之中。
在《艺术学院1994》这部作品中,每一帧精心绘制的手绘画面都展现出了1994年青春的影子,同时也揭示了那位制片人、那位动画导演对于艺术电影不懈的热爱与追求。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杨城与刘健在商业电影的激烈竞争中,依然坚持创作出了他们内心所追求的电影作品。
这种坚持,或许就是中国艺术电影最宝贵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