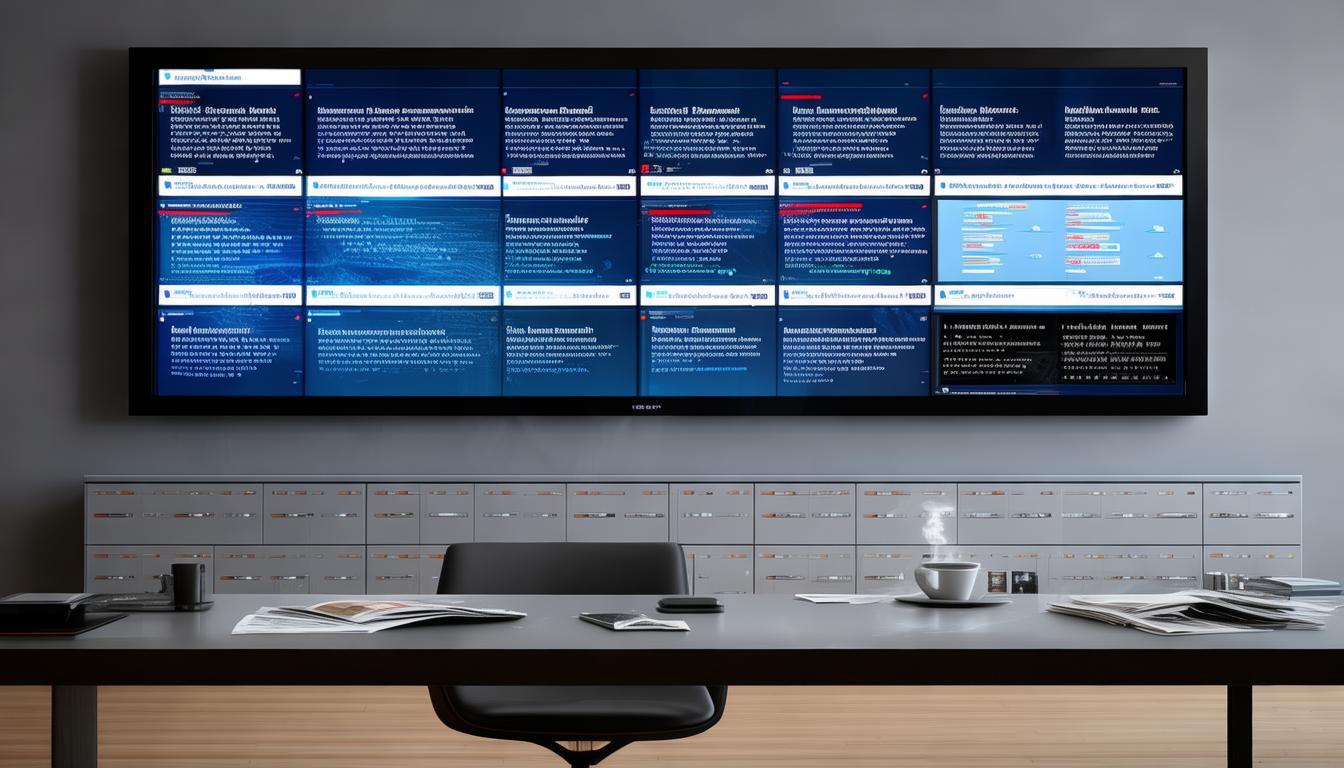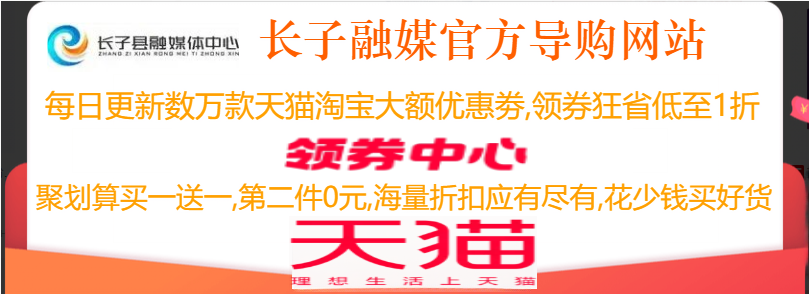本文在参考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融入了作者的个人见解进行创作,并在文章结尾部分对所引用的文献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注明。
(夜入宫门)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时间,是酉时。
酉时,也就是傍晚,五点到七点之间。
就在那时,一个行踪诡秘的人影,骤然间在紫禁城的慈庆宫现身。
慈庆宫,这座明朝时期在紫禁城内建造的宫殿,其址位于东华门内。然而,到了清朝时期,它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毁,不复存在。随后,清朝在慈庆宫的原址上,又新建了一座名为南三所的宫殿。
当时慈庆宫中居住的,乃是大明帝国的储君朱常洛,他的身份尊贵,令人瞩目。
在这封建时代,皇帝之下,便是太子一人,他日后将继承皇位,地位自然尊贵无比。因此,这位太子的居所,不论其他,其安保措施必然是相当周全的。
慈庆宫门口忽然出现了一个男子,他身着黑色衣衫,手持一根木棍,据记载,这根木棍是枣木制成,质地坚硬,坚固无比。更为奇特的是,他脸上还蒙着面纱。凭借这一身行头,我们可以断定,此人绝非宫中之人,他要么是盗贼,要么便是刺客。
只是,不论是偷窃者还是刺客,此人的心智似乎不甚健全,他选错了地点。你怎能闯入慈庆宫?那可是太子的居所,岂能轻易进入?那里必然布满了警卫,严密守护。若你在此行凶,实则无异于自寻死路。
然而您可能难以置信,当时的慈庆宫安保相当松懈,整个宫殿中仅有三五个侍卫,他们分散在各个角落,而宫门口更是空无一人。这样的安防措施甚至不如作者所居住的那处破旧的小屋,因此那些黑衣人携带凶器,轻易地便潜入了宫中。
宫中是否有人居住?嗯,宫中确实有人,不过仅仅是几位宫女以及两位年迈的太监。
这两位资深宦官中,有一位名叫李鉴,李鉴见有人到来,反应敏捷,立刻站起身来,准备对那身穿黑衣的人进行询问。
干嘛的?打哪儿来?在哪个宫里做事?到此何为?
那黑衣人并未开口,却迅速地迈出三步并作两步,紧接着,他猛地一拳朝李鉴的头部击去。
李鉴痛得倒地哀嚎,哎呦一声,周围的宫女和宦官们见状,顿时慌了神,以为有刺客闯入。众人纷纷大声呼喊,这一声喊叫,宫内外侍卫、太监们纷纷应声而来,场面混乱不堪,大家手忙脚乱,最终将那黑衣人制服。
夜幕降临,九时过半,那身黑衣的神秘人物,在众多太监的严密束缚中,最终落入了东华门驻城指挥官朱雄的掌控之中。
朱雄,他相当于现在的保安队长,而那些黑衣人则被转移到了保安室之中。
朱雄察觉到有人擅闯皇宫,潜入慈庆宫,竟还手持棍棒行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立即着手对那名黑衣人展开了审讯。
经审讯了解,该嫌疑人名叫张差,他来自蓟州,即现在的天津,关于其他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难以言表啊,您想想,朱雄身为武将,自然是以武力为本,审问张差时难免会动用刑具。尽管他挨了多次鞭打,却始终不肯吐露实情,除了姓名和籍贯之外,他的话乱七八糟,语无伦次。朱雄注视着他,总觉得他并非常人,恐怕精神上有些不正常。
(案犯张差)
张差的精神状况似乎确实有些异常,若非如此,别人闯入皇宫行凶时都携带着锋利的刀剑,携带匕首,而他竟然只带了一根棍子就闯了进去,这难道不是纯粹的有病吗?
朱雄感到困惑,他发现自己并不擅长审理案件,因此,他迅速将张差案件转交给了负责巡查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处理。
刘廷元虽为一名御史,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文化人士,其见识远胜于我。更为关键的是,他负责巡查皇城,而皇宫无疑是其巡视范围之内。
这类事物啊,若不称重,重量不足二两,可一旦称量,即便是一千斤或一万斤,也难以承受其重量。
思虑一番,整个皇城尽在你的刘廷元掌管之下,你又是如何治理的呢?你又是如何容许这样的人混入皇城,甚至在他人的监视之下擅自踏入皇宫的呢?
即便朱雄没有主动提供,刘廷元也迫切希望将这起案件揽入怀中,以确保自己能够牢牢把握住主导权。
刘廷元在审讯张差的过程中,大体上接受了朱雄的观点,即张差系精神病患者,他携带凶器擅自闯入皇宫的行为是出于无意识,加之其精神状况,其思维与行为均处于不可控状态,亦难以进行深入分析。
对刘廷元而言,这无疑是最佳的结果。若张差果真为反叛之徒,抑或持有特殊身份,怀揣着罪恶的企图,而他未能事先察觉,那便是他的失职,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只要认定张差精神有疾,刘廷元便无需担忧自己的职责。
谁能控制一个精神病呢?
或许刘廷元意图亲自处理此案,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他终究只是个巡城御史,权力有限。张差被捕的消息才刚传至慈庆宫,便已迅速传至内阁。此刻,万历皇帝肯定已经得知了这一情况。
此事非同小可,刘廷元不敢有所拖延,在审慎研究后得出初步结论,随即便将张差案件转交给了刑部处理。
知晓学问有高低,技艺各有专长,刑部乃我国最高司法机构,其职责正是处理此类事务,果不其然,张差案件在移交至刑部后,案情进展迅速。
刑部审讯张差的场面颇为热闹,其中不乏员外郎赵会桢、员外劳永嘉、郎中岳骏声等要员,然而他们均为副审。真正负责此案的主审官员,即直接对案件负责的,乃是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等人的连续审问让张差感到难以支撑,他在刑部所采用的装聋作哑的策略显然不再奏效,情势所迫,张差不得不继续交代。
他坦言,自己不过是蓟州的一名普通居民,平日里靠砍柴狩猎为生。去年秋季,他在荒野上收集了大量柴火,存放于庭院之中,既可备来年取暖,也可变卖换取钱财,无论哪种方式都无妨。然而,未曾料到的是,有两个邻居,一个名叫李自强,另一个名叫李万仓,这两个人平日里欺行霸市,横行乡里,他们欺负自己老实本分,竟在自家无人之际,一把火将院中木柴烧了个精光。
柴火已经燃尽,所幸自己归来得早,否则房子恐怕已被他们付之一炬。
张差表示,遭受了他们的侮辱后,他心中充满了愤怒,于是他打算前往京城告发此事。然而,由于不熟悉路线,他在京城四处徘徊,一时间不知该去何处告状。恰巧,他遇到了两个男子,他们十分热情。在得知张差的情况后,他们告诉他,若要告状,就必须去皇宫,而且不能空手而去,必须携带一些物品作为证据。
好吧,这里有一根棍子,你可以拿去,这根棍子实际上是用来生火的,等你到了……
宫里,你把棍子拿出来,别人就知道你有什么冤,有什么屈了。
(烈火熊熊)
他们交谈完毕,将木棍交于己手,并为我指引了前行之路。于是,我手握木棍踏入宫殿,意外地来到了慈庆宫。本欲向上级报告,然而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却将我误认为盗贼。无奈之下,我只能出手自卫。
这段叙述,听起来很合理,但仔细一样,很不合理。
你家柴火被他人点燃,若保长不闻不问,你可寻求县衙协助;若县衙亦无作为,你便可以前往府衙求助;若府衙亦无能为力,你甚至可直赴京师,向大理寺或都察院申诉。你所能寻求帮助的人众多。邻居欺凌,柴火被夺,你便需上告朝廷,面见圣上。这岂不是在戏谑于我?
提及遇到两位善心之人,这似乎更是荒谬至极,究竟何种善心之人,能以神仙指引的方式,将你引领入皇宫呢?
刑部判定,张差所言纯属无稽之谈,强词夺理,实则等同于胡士相赞同了刘廷元早前的结论,即张差患有病症,疯疯癫癫地闯入皇宫,并无作案意图,缺乏目的性,更关键的是,无人指使,整个事件背后并无幕后之人操控。
刑部审理完毕,案件并未立即尘埃落定,究其原因,在于朝中部分官员对审理结果持有异议。
例如,刑部主事王之寀、大理寺右丞王士昌等人,以及行人司、工科等众多部门,都纷纷提出质疑,大家普遍觉得,这事儿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简单。
直觉告诉一些人,不对劲,就是不对劲。
王之寀领衔的官员们计划对张差进行再次审判,以期挖掘出更多未曾发现的新线索。
张差身为罪犯,对他施以刑罚自然有把握,定能把握分寸,绝无致其死地的可能。案件尚未了结,证据链尚不完整。即便万历皇帝不亲临朝堂,但作为一国之君,他必然关注此案进展。若张差不幸丧命,你将如何向皇帝交代?
你没法交代。
因此,张差显得有些肆无忌惮,他深知这些大臣们表面上看似凶狠,但实际上却不敢对他怎样。所以在最近的审讯过程中,他开始胡言乱语,当被问及真实意图时,他竟说起了天气不错,而当被询问是否受人指使时,他又表示希望自己能有个美好的夜晚梦境。
您表示,若您身居审判之位,面对这样的情况,您又能采取何种措施,又能对他有何作为?实际上,似乎并无太多有效的应对策略。
王之寀注意到,这位名叫王之寀的人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在与张差共处数日后,他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每当牢房里分发食物时,张差总是表现得异常积极,他吃得相当多,甚至一粒米都不剩。
王之寀瞧见这情形,心想:既然他这么爱吃,那定是担心挨饿。于是,他心生一计,便恐吓张差,对他说:“你整天待在牢里,郢书燕说,驴唇不对马嘴,分明是不老实。既然如此,那我就从明天起,不再给你提供食物,让你尝尝饥饿的滋味。等你老实交代了,我自然会给你饭吃。若你仍旧顽抗不化,那我就只能让你饿死在这牢中了。”
击蛇需击其要害,铲除祸患必除其根本。你提及欲处决张差,张差或许并不畏惧,毕竟他已陷入绝境,料想无论如何都是一死。然而,若你让他经受饥饿,直至饿死,那对他而言将更为痛苦,远甚于直接了结其生命。故而,王之寀一吓唬他,他立刻改变了态度,不再愚笨,也不再狂乱,而是老老实实地供述了自己的来由。他承认,自己之所以前来告状,是因为邻居欺凌,柴火被烧,实则并非如此。实际上,不久前,有两位公公找上了他,将他带到京师,供他吃住,今日给银,明日赠金。他们并非无偿施舍,而是要求他帮忙办事。他们给了他一根棍子,并提供了皇宫的路线图,指示他依照地图潜入慈庆宫,见到身着黄衣之人便行击打,最好是将其击倒。
我说若是将人击毙,难道就不会有人命之虞?那两位公公却道无需担忧,他们声称自己神通广大,即便我导致他人丧命,也能确保我安然无恙。而且,他们还承诺,只要我将此事妥善处理,还将额外赐予我一片土地作为奖赏。
张差话音刚落,饭已经端上桌,然而王之寀却无法入口,更不用说进食了,他被吓得连一口水都难以吞咽。
(忧愁储君)
一见到身穿衣物的身影,便要出手攻击,务必将其彻底击败,天哪,在这慈庆宫中,能身着服饰的,难道不是只有太子朱常洛一人吗?
说白了,张差就是一个单兵刺客,他是要刺杀太子啊。
宫中宦官竟敢指使外人擅自闯入宫殿行凶,此事已令人震惊,简直丧尽天良。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敢对太子下手,简直是疯了!
这已非单纯的治安事件,亦非重大要案,而是演变成了一宗关乎国家根本的严重案件。

若真是那两个奴才在暗中作祟,他们若是毫无君臣父子之礼也就罢了,然而即便用十二指肠去推测,也难以想象两个宦官,竟能有如此深远的计谋,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说白了,宦官的背后,另有人指使啊。
而且,幕后主使者的身份已经逐渐显现,显而易见,因为庞保和刘成,他们不仅是万历皇帝宠妃郑贵妃的亲信,更是她的心腹之人。
简而言之,揭开真相,张差行刺朱常洛的背后,真正的策划者乃是郑贵妃,一切行径均是她所指使。
这不禁让人疑惑,皇帝的贵妃与太子之间,究竟有何争执?竟至于让郑贵妃行凶?他们并非同在一家机构工作,彼此之间并无直接的竞争关系。
确实,郑贵妃与朱常洛之间并无直接冲突,他们之间无需相互竞争。然而,问题在于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与朱常洛却是势不两立,他们之间的竞争可谓是激烈异常。
朱常洵与朱常洛均为万历之子,然而朱常洵乃郑贵妃所出。万历妃嫔众多,然皇帝独钟郑贵妃,对其宠爱有加,独享特殊恩宠。因此,皇帝对郑贵妃之子朱常洵宠爱备至,一心想将其立为太子。
明朝的皇位继承,一般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嫡系,指的是嫡出之子,即由皇后所生;若非皇后所出,则称为庶出,亦即庶子。
若皇帝拥有嫡出的皇子,那么自当立他为太子,其余庶出之子则需退居次席。然而,万历帝并无嫡子,因此太子的位置不得不从庶出皇子中挑选。尽管如此,仍需依照长子继承的规矩,即年龄较大的皇子优先被选为太子。
万历皇帝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然而朱常洵却是庶出的第三子,而朱常洛则是庶出的长子,这种情形显然与祖制规定相悖。
(三子常洵)
自然有不少读者会这样讲,万历身为皇帝,乃是一国之君,他的话分量极重,所有人的行动都必须遵从皇帝的意志,任何人的反抗都无法改变皇帝的决策,至于太子人选,归根结底,还是由万历皇帝最终定夺。
其它朝代可能皇帝自己就定了,但是明朝比较特殊,不太行。
为何要说明朝不行呢?那是因为明朝的官员,尤其是文职官员,他们性格固执,内心深处只认同长子继承制,而且他们还有意与皇帝对抗,期望皇帝能够重视并听从文官的建议。因此,每当万历皇帝提出要立朱常洵为太子时,大臣们便会激烈反对,坚持认为只能立朱常洛为太子。
明朝时期,君臣之间因册立太子一事引发纷争,此事件在史册上占据一席之地,被称作国本之争。作者有机会单独详细讲述。总之,当时文官们无所畏惧,既不畏战,也不惧死,更不惧失官,他们结成党派,形成小团体,人多势众,持续向万历皇帝施加压力。万历皇帝也并非轻易妥协,他在过去十余年间,曾罢免过首辅,停职过尚书,杖责过法司官员,仅因立太子一事,便整治了众多文官。然而,即便如此,万历皇帝也未能如愿以偿,他尝试过软硬兼施,分化拉拢,甚至不惜低声下气,以牺牲帝王尊严为代价,恳求文官们支持,但文官们依然坚定地支持朱常洛,排斥朱常洵。
后来万历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把朱常洛立为了太子。
皇帝费尽心力,力图将朱常洵确立为太子,这背后显然与郑贵妃的私房话脱不了干系。万历帝对朱常洵成为太子的渴望程度,郑贵妃对朱常洵的偏爱恐怕还要超出万历帝十倍不止。
然而,由于文官之间的争斗,以及其他诸多因素,这对夫妻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从这一视角审视,郑贵妃对朱常洛的感情可谓是深恶痛绝,痛恨至极,她极有可能因为发泄怒火、心怀嫉妒而雇佣刺客行凶。
况且,若能成功除掉朱常洛,那么朱常洵的机会自然又会浮现。毕竟,实施暗杀的人,往往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张差已经供出了庞保和刘成,此事众人皆知,无需多言,显然是郑贵妃所为。只要智商达标,人人都能看穿这一点。
王之寀虽身为一名低级官员,却性格刚烈,在查得这一结果后,他迅速将其公之于众,直指郑贵妃为矛头所向。
此刻的郑贵妃,仿佛面对强敌,若想洗清自己的嫌疑,恐怕只能投身护城河了。
张差的供述、舆论的巨大压力,以及诸多证据均指向,我就是那个指使心腹宦官雇佣刺客潜入皇宫,意图加害太子的阴险狠毒的妇人。
这罪名一旦坐实了,别说郑贵妃自己,九族恐怕都要消消乐。
天降灾祸尚可宽恕,若是自招祸端则难以存活,按理说,郑贵妃早已命丧黄泉,无需再作无谓的挣扎,事实既已昭然若揭,只需静待皇帝的惩罚降临即可。
郑贵妃并未甘心认输,她的思维敏捷,迅速作出决定,她认为不能被动等待,于是她立即前往拜见万历皇帝。
在觐见万历皇帝之后,郑贵妃泪如雨下,痛哭流涕,坚称自己无辜,断然否认指使他人刺杀太子的指控。
万历开口了,尽管我姓朱,但你可别真把我当作一头猪,这难道不是你指使的吗?你心里难道还没有一点数吗?
(万历皇帝)
若是这位作者身处万历年间,他必定会将郑贵妃废除,又有谁能够忍受一个心肠歹毒的女子企图加害于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至于杀不杀,按本朝的国法办。
然而,问题在于,这位作者并非真正的万历皇帝,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对郑贵妃的宠爱已经到了极点,生怕轻轻一碰便会伤到,连放在嘴里都要小心呵护。尽管皇帝明知道郑贵妃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却对她没有丝毫责备之词。他只是说,如今外界舆论纷纷,对你极为不利,众人都怀疑是你所为,你简简单单几句话也难以澄清,即便你找我,也是无济于事。天下悠悠众口,我又怎能一一堵上呢?
郑贵妃焦急地询问,"亲爱的,这该如何是好呢?你必须救我,否则我岂不是要名誉扫地了吗?"
万历回答:亲亲,这边建议你去找一下当事人朱常洛。
皇帝对情况看得相当透彻,治疗心疾还需用针对心疾的药方,解铃还需系铃人,朱常洛身为当事人,是直接的受害者,你若能找到他,只要他愿意为你辩护,声称此事并非你所为,那么他人也就不会再质疑,你便能确保自身安全。
郑贵妃言犹在耳之际,急忙赶往慈庆宫,见到太子朱常洛后,哭声愈发凄厉,泣不成声,她一边哭泣一边辩解,声称自己从未有过伤害你的意图,请你相信我,我对你的关爱与常洵无异。
朱常洛开口了,我根本就不信你,除了你,还能有谁?你这个人啊,实在是太过分了,你简直就是用毒鸟做媒,用毒蛇做心,你的心肠坏透了。现在你还在这装好人,真是让我恶心,呸!
当然了,这也只能是心里话了。
自郑贵妃步入慈庆宫的那刻起,朱常洛便察觉到,那位素来对自己态度冷淡、漠不关心的父皇,此次亦无意协助自己伸张正义。
朱常洛明白的,这就是父亲让她来的。
作为儿子,又身为太子,难道真的忍心看父亲的妾室难堪,违背父亲的旨意吗?
他敢吗?
轻叹一声,朱常洛脸上洋溢着笑容,他搀扶起那演技足以赢得奥斯卡奖项的郑贵妃,并向她郑重承诺:
此事与贵妃娘娘无关,今后我亦将禁止他人对此事进行讨论。
把郑贵妃送走之后,朱常洛陷入了回忆。
亲生母亲名为王恭妃,她出身于宫女,父亲对她颇为轻视,认为她身份低微,连带对我也不屑一顾。
父亲将母亲囚禁于一座隐蔽的宫殿之内,供给的衣物和食物极为有限,身边几乎无仆人伺候,更不用说派遣人手照料,他自己也受到严格约束,与母亲相见的机会极为罕见。
母亲无法饱食,无法畅饮,体质孱弱,还遭受父亲的冷漠对待,加之对儿子的深切思念,于是她终日以泪洗面,最终竟至失明。
郑贵妃经常派人去羞辱她的母亲,时常动手动脚,言辞粗鲁,以至于在母亲有生之年,她未曾有过一天安宁和快乐的日子。
至于我自身,父亲从未关心过我的日常生活,更不曾请教师前来为我授课。身为太子,我想要见到父亲一面,其难度堪比登天。而我的三弟朱常洵却屡受赏赐。父亲、郑贵妃、朱常洵,他们三人一家和睦,共享天伦之乐。至于我,又有谁会在意呢?
数日过后,庞保与刘成在皇宫之内被秘密处决,执行这一暗杀令的,竟然是万历帝本人。
(贵妃郑氏)
历史,有时候真的很讽刺。
谈及万历,他曾对王恭妃和朱常洛抱有偏见,视王恭妃为出身低微的宫女,将她归入贱籍之列。然而,他是否曾意识到,他的母亲李太后,也曾是宫女,被隆庆帝宠爱,这才有了他——他自己同样是宫女所生。
郑贵妃自私自利,她凭借情感操控万历,费尽心机,想方设法地企图除掉朱常洛,以便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登上太子宝座。即便是在朱常洛登基后不到一个月便突然去世,这也与郑贵妃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所谓的红丸案,作者将在后续内容中详述)。
郑贵妃对儿子朱常洵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她全心全意地爱护着他。然而,在事业方面,她未能满足儿子的愿望,于是她转而尽力在财富上给予补偿。因此,她费尽心思,促使万历皇帝将儿子封为福王,赐予他无尽的金银财宝,并且将洛阳这一繁华富庶之地作为他的驻藩。
郑贵妃深信,这样一来便能一劳永逸,她的儿子余生将沉浸在无尽的荣华富贵与安逸之中。然而,她未曾料到,数十年后,一位名叫李自成的人将打开洛阳的城门,以她最珍视、最怜爱的儿子为代价,来清算她一生的罪孽...
参考资料:
《泰昌朝记事》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明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
雒雪.王之寀与梃击案研究.黑龙江大学,2017
郭永臻.《三朝要典》研究.山东大学,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