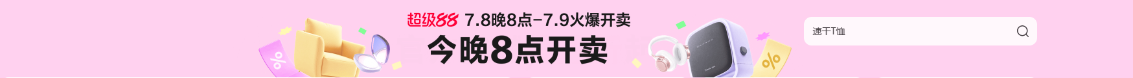腓尼基计划
The Phoenician Scheme
爆炸的缺口
起初,这里是一个规整的、近似于正方形的空间;然而,就在此刻,四边形的一角突然被炸裂,那些无辜的龙套以及其他物品瞬间化为灰烬,尸体碎片被强大的气压猛烈地轰出窗外,而墙上溅射的血液则形成了一幅自动生成的画作。
一开始,韦斯·安德森的这部新作便与炸弹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其中手榴弹更是被赋予了温馨的赠品之意。这一卡通式的暴力画面并未使我们感到威胁,原因在于我们深知,安德森塑造的角色仅存在于虚构的空中,连飞机也并非真正的实体,因此它带来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喜剧效果,同时也让本尼西奥·德尔·托罗得以在奇迹般的迫降中幸存(毕竟,这里并非《碟中谍》的世界,那里人物从空中坠落所蕴含的物理意义已经超越了剧情本身)。在镜头的构建过程中,爆炸可能又揭示了一个新的议题:除了野心家的飞机驾驶舱外,那被炸裂的缺口同样触及了封闭画框的内在——在画外,或许还存在着一个名为“现实世界”的领域。
《腓尼基计划》爆炸开头
自《布达佩斯大饭店》问世后,韦斯·安德森在普通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有所下滑,这一变化与他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电影中逐渐增强的政治色彩紧密相连。
随着安德森的电影逐渐深入一个独立的符号领域,他所关注的现实世界也在不断演变(反之亦然):他虚构出未曾存在的王国、政治体系与权力机构、小人物的抗争以及大人物的悔悟。在《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作品中,安德森以怀旧的笔触,借助乡愁的时态描绘了纳粹时代的细微人文情怀,流露出对欧洲大陆往昔传统的眷恋。然而,这种温馨的糖衣在随后的定格动画《犬之岛》中迅速剥落,结尾所呈现的不再是怀旧之情,而是一连串令人不安的余音:旧政权被新势力所替代,在权力争夺中受伤的狗儿被当作烈士献祭,它们隐居于自家的墓穴之下,再次遭受囚禁之苦。
《布达佩斯大饭店》
《犬之岛》
镜头所捕捉的线路、空间与语言秩序的精心布局,安德森所展现的“风格”不仅揭示了秩序机器的构成要素,更是该机器的化身,既是乌托邦的理想,亦是其对立面。即便观众未曾期待在安德森的作品中探寻“政治”元素,然而导演本人对形式的狂热却似乎将他引向了这一领域。尽管起初这不过是如同《青春年少》中的高中生或《月升王国》里的童子军那样,对打破常规秩序的幼稚反叛幻想,带有一种孩童般的惊悚感。
我们越来越难以被安德森的作品所触动,这或许是因为作者本人也在逐渐摒弃那种和谐的情感流露。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叙事手法是否能够持续激发高涨的热情,从而为电影和观众提供充分的情感释放。在真人电影中如何展现现实世界的政治,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安德森或许意识到,他曾经采用的方法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束缚。鉴于完全摆脱这一模式的可能性似乎愈发渺茫,作者因而决定持续加固其框架,并尝试探究其潜能的边界。
《法兰西特派》与《小行星城》均凭借其独特的形式与叙述力量脱颖而出,无论是描绘法国的一座小城,还是疫情隔离背景下的美国西部,影片所展现的,无疑是一群被困的人物,他们身处可见的囚笼,同时也被无形情感所束缚。进入改编自罗尔德·达尔的《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及外三篇》的世界,影片以几位固定演员扮演的角色不断变换,以及平面的手工布景为背景,展现出一种戏剧作坊的独特质感。在这些短片中,人物们表演着肉眼难以察觉的绝技,而影片在精致的外表之下,对视觉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法兰西特派》
《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
或许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腓尼基计划》这部或许旨在展现宏大野心的电影,却常常流露出一种随意的气息,并呈现出一种重复带来的效果。影片的故事情节紧密围绕角色的情感发展,自身演变为一连串的交易与协议,无论是针对CIA的合约间谍,还是陷入家庭协议的父女,角色们都自愿受制于这些条款,接受所承担的责任。
德尔·托罗扮演的“Zsa-zsa”在影片中以报纸上常见的实业家形象出现,化身为《公民凯恩》或《阿卡丁先生》那样的神秘角色,通过夸张的语气激发观众对其背景的好奇。与《亨利·休格》中描述主角疯狂敛财的片段相较,这部新片的语气显得更为内敛和沉稳,尽管叙述上显得活力不足,却隐含着更深层次的含义: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因此无法完全洞察其本质。在经典的好莱坞影片里,不论导演是刘别谦、斯特罗海姆还是普雷斯顿·斯特奇斯,资本主义运作和阶级关系的描绘都建立在一种表演之上。这类电影只能在宽敞的摄影棚内拍摄,演员们通过服装、化妆和姿态来模拟利益链条的布局和调度。
《公民凯恩》
《阿卡丁先生》

或许,影片灵感的源泉,正是德尔·托罗那步履维艰的足迹,与之相呼应的,是藏于鞋盒中的档案资料。这些看似理性的叙事素材,为影片带来了创作的契机——并非指影片中的经济空缺,而是那些从中流淌而出的伤痕。正因为如此,《腓尼基计划》并未力求成为一部典型的“大亨电影”,围绕这位资本家的描绘显得尤为静态,人物在众多临时搭建的空间里进行的活动与策略安排并不具备太多冒险性(正如安德森在与《电影手册》的访谈中所提及,诸如“大富翁”等桌面游戏对影片创作产生了影响)。在图像之中,一旦出现爆炸,便如同发现了“刺点”,这不仅直观地展现了破坏的形象(如疤痕、弹孔、残骸),而在某些瞬间,“爆炸”却可能悄无声息,甚至呈现出一种坚固至极、难以破解的状态。
银幕呈近似方形,其上布满了负空间,这现象既缘于影片未明示观众视线应聚焦于画框的何方,亦因画面本身所呈现的真实广阔空白——如慵懒的云层与沙漠般的色块;令人目眩的阿拉伯图案;宽敞客厅那高挑的屋顶,让人不禁联想到摄影棚的墙面;甚至导演从顶级画廊租借的杰作(从雷诺阿至马格利特),也似乎随意地散布在宅邸各处——这些艺术引用出人意料地缺乏叙事功能,它们绝不可能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的苹果与男孩那样,成为具有护身符意义的麦高芬(电影中的艺术品并非由虚构角色严密守护,而是由现实中的艺术馆专员负责保管),这些布置与其说是炫耀奢华或是对艺术史的致敬,不如说在图像中隐含了一些转瞬即逝的秘密缝隙,一些逃离虚构历史的证据。
《腓尼基计划》
当然,对于“Zsa-zsa”来说,收藏杰作实属顺理成章之举,而财富,或者说金钱的积累,呈现出一种平稳且近乎自动的写作节奏,不受任何意外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影片本身具备了游戏的特性。他多次强调:“我个人感到非常安心。”
自然,当电影持续保持这种总体上的、近乎严酷的稳定节奏时,其中所展现出的那份质朴的乐趣便显得尤为值得我们去有意识地发现。在叙事过程中,它屡遭怪异姿态的阻挠,尽管这些插曲并未对电影的整体节奏带来太大的影响:,
此片看似间谍与商业斗争的影片,实则讲述了一段父女和解的家庭故事。或许,迈克尔·塞拉的昆虫知识讲座对其产生了影响,使得影片的科普价值被削弱。同时,塞拉那独特的挪威口音也使得这一表演的科普意义进一步被淡化。此外,米娅·塞普雷顿(饰演“Zsa-zsa”的疏远女儿和继承人)的出色表现,似乎在讽刺这一切。与往常的安德森风格群戏不同,此番除了那对父女以及“教授”所组成的三人团队,绝大多数的明星“玩家”们仅扮演着繁琐仪式的旁观者角色,他们在为数不多的场景中移动的棋子极为有限。这些扮演着其他权势寡头角色的演员,仅进行了一些基础的物质交换:一场胜负差距极大的篮球比赛、有人为他人挡下子弹或捐献血液、一场由家族一手操办的近亲婚姻;而影片标题所提及的“计划”,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一个庞大的模型。
《腓尼基计划》
引人注目的是,不止一位人士谈到了本片与去年那部“大亨电影”之间的联系,这种类型的作品在保守主义重新兴起的背景下,似乎恰逢其时地迎来了新的生机。
但我们从中需要指认的是什么?
安德森的作品通过游戏化的手法再次印证了金钱世界的法则,同时,电影不自觉地串联起了弗朗西斯·科波拉的《大都会》里那同样虚幻的乌托邦构想——弗朗西斯的儿子罗曼·科波拉曾是安德森的长期编剧——后者亦试图将一个古老国度与当代讽刺剧相结合,然而,两者的雄心壮志多少都未能如愿以偿。
科波拉的影视作品中,虚拟场景的数量持续攀升,导致叙事结构逐渐瓦解。然而,与此同时,过度的野心也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坎普式趣味。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安德森的电影中,主角们不断从高空坠落却奇迹般地生还,而科波拉的作品中,主角们却在坠落前便停止了时间的流逝;《大都会》这部电影最终让时间支离破碎,而《腓尼基计划》则让时间落到了地面,直面其留下的空白。
《大都会》
若这部作品标志着安德森对线性叙事手法的回归,那么,鉴于线性时间与死亡降临紧密相连,影片中所呈现的线性时间流中充斥着近乎暴力的省略。从主角们的每一次离场与对话,到那些戏剧性的瞬间戛然而止,再到“Zsa-zsa”每次从天堂重返人间,穿梭于生死之间的黑白场景,电影的核心主题无疑是促使一位冷漠的父亲直面自己在时间中留下的裂痕:去探究两个镜头之间发生了什么,去思考在一段祈祷的时间里,是否有所改变。
在电影即将落幕的短短几秒片段中,当“Zsa-zsa”终于直面她多年来不敢正视的对手,同时也是她过往的自我时,几幅尘封在旧鞋盒中的陈年照片在银幕上迅速闪现,伴随着最后一次爆炸声——游戏本身被彻底摧毁,主角被迫退场。
《腓尼基计划》
在电影尾声,身份已恢复为劳动者的“Zsa-zsa”仅在其小餐馆内留下了康定斯基的《第8号作品》一幅画作——或许只是复制品。画中,各种颜色、大小不一的圆形、三角形与线条交织,于复杂的外表之下,透露出一种几何的规律性。正如电影的导演,参与一场金钱的游戏,就如同对艺术品进行一段时间的借用,而最终,这些艺术品还是会回到博物馆的收藏之中。随着这部家庭情感剧的落幕,那些签订的协议亦逐一失效,影片结尾的和谐团圆场景重拾了观众的观影错觉,我们或许会误以为导演通过这场政治游戏能揭示现实的裂痕,将他所构建的虚构世界与银幕之外的现实世界相连,然而,故事最终依旧平淡收场——在这里,形式已被耗尽,而形式本身承载了安德森电影的核心价值。
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安德森一旦重新拾起某个故事或形象,其呈现的形式仍将向我们揭示该故事中的秩序(在戛纳,他暗示即将拍摄的新片将融入“黑暗”元素):他的近期作品都在探讨被形式所包裹的秩序。以《腓尼基计划》为例,它似乎是对线性叙事的一种回归,并尝试卸下其外衣。或许在下次的创作中,那些充满危险的因素将真正颠覆风格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