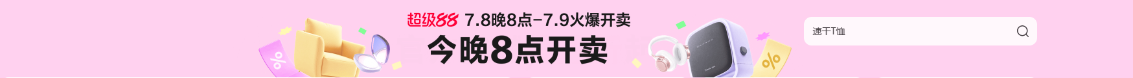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High On Films(2021年6月2日)
电影,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正逐渐沦为政治的追随者,未来恐怕也难以摆脱这一命运。回顾历史,电影在20世纪专制势力初露头角之时崭露头角,那时人们认为电影所具有的民粹主义魅力,比书面文字更能迅速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但事实表明,在持续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那些以宣传为目的的艺术作品,其存在时间往往是短暂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宣传片虽与社会政治脱节,却对电影自身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贡献甚至超越了其他所有类型的电影。莱妮·里芬施塔尔运用长焦镜头和低角度拍摄手法,对1934年纳粹党代会的场景进行了深刻描绘;而爱森斯坦则巧妙地运用蒙太奇手法和隐喻画面,这些手法和画面已经成为了电影语言的固有元素。
《意志的胜利》
他们的创作不追随传统,却扎根于本国民族特色之中,这些作品既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意识形态的结晶。换句话说,对于这些电影人而言,创作的根基在于他们的存在,而非艺术性的附属。
1964年,美国政府在与古巴因猪湾事件断交三年之后,莫斯科电影厂携手古巴艺术与工业电影研究所(ICAIC)共同制作了一部影片——苏联试图争取古巴民众的支持。该影片旨在展现古巴革命的辉煌成就以及社会主义政府的合法性。
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在塔可夫斯基之前,堪称苏联电影界的荣耀,他被委以重任,执导了名为《我是古巴》的电影。该片的宗旨,在于揭示美国殖民统治之下,古巴社会各阶层如何形成,以及广大民众所面临的贫困困境。此片无疑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它成为了在国际上传播社会主义理念的重要途径。
《我是古巴》
影片以俯瞰古巴森林的画面作为开头,紧接着,观众目睹了一个渔村的景象,之后则是繁华都市哈瓦那的风貌。一个自称为“古巴之声”的嗓音,以诗歌的韵律,描绘了世界其他国家如何透过美国帝国主义的视角,将古巴描绘成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度假天堂,却鲜少将其视为一个真正属于古巴人民的独立国度。
《我是古巴》自始至终都彰显了电影的核心在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影片续而展开四个独立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不紧密关联着美国对古巴民众的剥削。在这些故事里,我们都能听到“古巴之声”,它在每个故事的尾声中回响。
为了凸显这一古巴特色,影片中的自然风光经过了别具一格的视觉效果处理。卡拉托佐夫特地从苏联国防部队引进了一种独特的红外感光胶片,使得画面呈现出一种“木质感”——树叶闪烁着雪白的光芒,能够反射光线,而树木和其他植物则散发出荧光,这种“木质感”在片头展现的渔村和船夫场景中尤为突出。
在哈瓦那的首场演出中,摄像机沿着屋顶缓缓下降直至泳池深处。在《我是古巴》这部影片里,短短几分钟内便出现了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复杂镜头,这些画面流露出一种独特的动态美,令观众及资深电影从业者都感到震惊。还有一幕尤为艰难的镜头,描绘了一位农民在意识到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即将被雇主没收,而雇主已将土地出售给联合水果公司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焚毁自己的庄稼和住所。摄像机紧随那位农夫,他点燃了房屋,倒在了田野之中,镜头聚焦于被烟雾笼罩的苍穹。

在这部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镜头语言尤为突出,画面镜头从熙熙攘攘的街道缓缓上升,直至抵达一间雪茄制造车间,穿梭于各个房间之间,最终从窗户飞出,在空中环绕街道,俯瞰下方正在进行中的烈士葬礼仪式。在纪念碑的阶梯上,一场难忘的抗议活动映入眼帘,让人联想到《战舰波将金号》中奥德萨阶梯的场景:烟雾弥漫,水火肆虐,混乱接踵而至,画面中的混乱氛围深入人心。这种手法在《我是古巴》上映之前鲜为人知;它摒弃了传统镜头的视角、构图、遮挡和移动,以一种激进的姿态,展现了奥逊·威尔斯式的运镜风格。
《我是古巴》的每一个镜头都持续了很长时间,且内容丰富复杂,若将它们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往往难以察觉其中的美感。然而,若在播放过程中按下暂停键,每一帧画面都仿佛是一幅迷人的风景画。影片将古巴的美丽融入叙事之中,这不仅激发了民族情感,而且使用广角镜头的意义也因此变得更加深刻。
卡拉托佐夫的构思在于全面呈现古巴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平凡还是不甚美观的景象,力求尽可能全面地描绘这个世界,以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能够不时地发现其美丽所在,而非被纷繁复杂的镜头所淹没。
“诗电影”是一种纯粹依靠视听元素构建的电影形式,它能够独立而完美地叙述故事,无需字幕或旁白来阐释细节。此类电影还擅长传达一种细腻的情感表达。它并非一个客观的影视类别,其根本宗旨在于将电影这一媒介,以最纯净的方式呈现给观众。电影常常被视为最纯粹、最能体现人类本性的艺术形式。
形容词堪称赋予诗电影至高无上的赞誉,这源于其对媒介根本性问题的深刻探讨。众多投身于诗电影创作的导演们,虽各有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却共享一个共性,即通过视觉、画面以及音乐来叙述故事。
《我是古巴》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显著优点在于独特的风格和卡拉托佐夫坚定不移的视角。影片中的旁白或许显得较为强硬,然而鉴于影片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它必须与诗意电影的一些理念有所冲突,并通过旁白来提升画面的诗意效果。
与那位明显是严格形式主义者的爱森斯坦相比,卡拉托佐夫的拍摄手法从未被技术上的细枝末节所束缚。在影片中,角色的行动仿佛与现实世界别无二致,他们的走动几乎不受摄像机镜头的约束。该片充满了自发性的气息,这使得它更像是戈达尔早期那些黑白影片的风格,而非卡拉托佐夫在苏联的同行们所追求的表现手法。
然而,事实本身便拥有极强的说服力。电影中的每一个画面,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拍摄。不知为何,这些画面中蕴含着一种现代感,革命胜利的喜悦与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共同推动了革命,这也使得镜头技术的复杂度得到了降低。
1964年,《我是古巴》一经上映便遭禁映。然而,直至90年代,马丁·斯科塞斯偶然间发现了这部影片,并与科波拉携手将其呈现于世人面前。他们共同认可了其卓越的艺术价值,使得这部影片终于得以再次与观众见面。
苏联人觉得影片所传达的内容过于平和,古巴人因影片中对他们的刻板描绘而感到被冒犯,而西方国家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关系,对此并未给予关注。卡拉托佐夫所处的社会主义体制塑造了他,然而,正是他对这一体制的挑战,无意中促成了《我是古巴》这部风格迥异的作品的诞生。
该影片所展现的自由与自主属性,很可能对苏联的政治宣传影片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电影的开篇,镜头从高处俯瞰古巴的森林,呈现出一片宁静的画面,然而,在故事的尾声,这种宁静被彻底打破。
我们同样观察到,随着对极端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威权政府甚至能够抑制那些宣扬其意识形态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却蕴含着艺术中最具个性化的元素——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