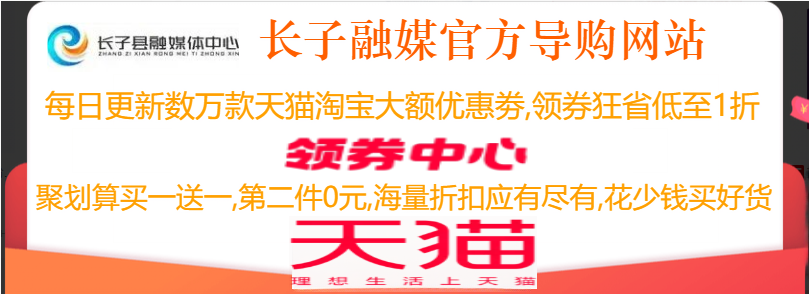雍正十三年深秋,紫禁城内哀声震天,丧钟悠扬地回荡在苍穹之上。那位凭借雷霆手段执掌朝政长达十三载的皇帝,竟在此时溘然长逝,驾鹤西归。
消息抵达杭州,那位让众多贪官心生畏惧的李卫,正凝视着闪烁的烛光陷入沉思。突然间,他身体一震,手中的热酒不慎洒落,湿透了价值不菲的蟒袍前襟。
他没有动手擦拭,目光却紧紧锁定那片迅速扩散的深色酒痕,那酒痕仿佛是他命运突然跌落的缩影。
小吏崛起
李卫出身并不显赫,在康熙五十六年,他的家庭不惜花费银两,为他捐了一个兵部员外郎的职位。这样的起点,在那些以科举为正途的官场人士眼中,几乎无法引起重视。然而,他却意外地遇到了面容冷峻、心肠冷漠的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胤禛当时负责管理户部,是个对瑕疵零容忍的人。他发现云南盐政的账目混乱不堪,盐税的亏空数额令人震惊。那些被派去核查账目的官员,要么是被地方官员蒙蔽而回,要么是被盐商用金钱收买,闭上了嘴巴。
胤禛眉头紧蹙之际,李卫这位冒失鬼挺身而出:“王爷,不如让我来试一试?”
“你?一个捐来的官儿?”
李卫梗着脖子说道:“我虽不懂得那些复杂繁琐的文书,却分得清银子的颜色,是黑是白一目了然!”
李卫抵达云南后,行为举止出乎意料。他全然不顾官场中的常规礼节和人际交往的复杂关系。面对盐商们递上的丰厚礼物,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说了句:“拿走东西,留下账本!”然后立刻投身于如山般堆放的旧账之中,带着几个亲信日夜不停地查阅。
两个月后,他携带着几本厚重的账册返回京城汇报,账册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问题,条理井然,证据充分。贪污的数额、手段,一切都一目了然。
胤禛凝视着这实实在在的“硬货”,又瞧见李卫熬得通红的眼睛,心中已然明了:此人,堪称一块既坚硬又粗犷的磨刀之石。
雍正元年,李卫在直隶驿传道的职务上,察觉到大名府的知府曾逢圣以及知县王游存在亏空钱粮的问题。他毫不犹豫,立即上报朝廷。朝廷派遣官员前来调查,李卫则紧追不舍,寸步不退,最终成功揭露了这两个贪官。
后来,他成为了浙江的总督。在江南,盐枭朱福根的势力错综复杂,私盐贩子众多,气焰十分嚣张。地方官员对此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李卫上任后,立即派遣军队,对河道和关卡实施封锁,并亲自驻守现场指挥抓捕行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朱福根的犯罪团伙便销声匿迹。盐枭们对他恨之入骨,甚至编出了顺口溜来诅咒他,称他为“活阎王”。
大树倾倒
雍正十三年,急报如风驰电掣般涌入杭州城。李卫在总督府内,埋头于案牍之间审阅文件,忽然接到密信。那信使全身尽湿,语声颤抖,几乎无法成句:“大人,万岁爷……他……他驾崩了!”
李卫只觉脑袋“嗡”的一声巨响,幸亏紧握着冰冷的桌案,才没有失去平衡倒下。那份薄薄的、却沉甸甸的密报,那赋予他权力、信任和依靠的“主子”,如今已不复存在。
乾隆帝即位后,紫禁城内弥漫着一种新气象。这位年轻的皇帝充满活力,与父亲严厉急躁的风格截然不同,他倡导“宽容仁爱”,渴望亲近贤臣。对于像李卫这样固执己见、不懂得变通的“严酷官吏”,在新的朝政中自然被视为“陈规陋习”。
李卫在浙江任职期间,触怒了众多人物。那些曾经被他整治过的贪官污吏、地方上的豪强,察觉到了时局变动,于是纷纷聚集,将弹劾的奏章如同雪花般迅速送往新皇帝的御案。

乾隆审视着这些奏章,面无表情,只是轻描淡写地对身旁的大臣道:“李卫行事,勇猛果敢,但过于草率,不符合大臣的稳重。”
不久,一道命令抵达杭州:调任李卫返回京城,担任刑部尚书一职,实则是一种明升暗降的策略,剥夺了他原有的地方实际权力。
李卫重返京城,宛如一只失去栖息地的猛兽。在刑部衙门,他那果断坚决、直截了当的方法无法发挥效用。同事们表面上客气有礼,但眼中却流露出疏远与戒备。在朝廷的议事场合,他依照旧例据理力争,常常话音未落,便被婉转而坚定地驳回。
没有了雍正这一唯一的支柱,又受到新帝的暗中疏远,李卫的体态明显地衰弱了。往日那健壮的身躯,如今正迅速地变得消瘦。
乾隆三年十月末,那位令无数宵小之辈心生畏惧的杰出官员,精力耗尽,生命戛然而止,终年仅有五十一岁。自雍正帝驾崩以来,不过短短三年两个月的时间。
身后波澜
李卫离世,消息迅速传遍,江南众多曾受他恩泽的民众在私底下悄然落泪。尤其是浙江地区,杭州、嘉兴等地的百姓对他充满感激,他们暗中商讨,计划为这位“李大人”修建生祠,并设立庙宇以示祭祀。
这消息不知为何,传入了紫禁城乾隆皇帝的耳中。乾隆正忙着审阅奏章,一听到这件事,脸色顿时变得阴沉,“真是岂有此理!”
他起身站立,于殿堂之内焦躁不安地来回走了几步,手指向南方,声音严厉地说:“竟敢擅自以名宦自居,假托名号建立庙宇,接受无知百姓的香火祭拜,究竟是谁给了他这样的脸面!这是严重的越礼行为!实在太过分了!”
乾隆帝的愤怒并不仅仅源自于“越礼”之举,更深层次的是,他对前朝遗老遗少所产生的影响力感到忧虑,并且有意与其父雍正帝时期的一些严格政策保持距离。
李卫,作为雍正时期铁腕政治的显著标志之一,他的深得民心愈发凸显了雍正朝“严政”似乎有其合理性的观点。然而,对于正致力于树立“仁政”新形象的乾隆皇帝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
“传令!”乾隆语气坚定,“李卫并非通过科举途径出身,亦无显著文治成就,怎能依照官员祭祀的惯例被供奉?地方官员必须严格调查!对于任何私自设立祠堂祭祀李卫的行为,一律视为邪教!立即予以拆除!绝不允许此类恶习蔓延,扰乱视听!”
一经圣旨颁布,地方官员不敢有丝毫懈怠,那些刚刚搭建的简易庙宇,或是民众私下供奉的灵位,都遭到了破坏和清理。在杭州西湖畔,一座香火正旺的李公祠,遭到了衙役们的蛮横推倒,神主牌被粗暴地摧毁,供桌也被砸得粉碎。
李卫的名字,在乾隆的轻蔑之下,被无情地刻在了“庸奴”的耻辱牌上。他在任职期间所掀起的波澜壮阔,以及他为民众所办的诸多实事,似乎都随着那些被摧毁的庙宇,一同消逝在了乾隆朝刻意渲染的“宽仁”氛围之中。
乾隆对李卫的称呼“庸奴”透露出的冷漠,彻底熄灭了民间对这位“酷吏”所抱有的那丝渺茫的敬意。在帝王的权谋之下,李卫一生的功过是非被无情地压缩扭曲。
西湖畔那座被强制拆除的庙宇遗址,默默见证了这样一个法则:即便是在紫禁城那深邃莫测的棋局之中,即便是再锐利的棋子,也终究无法摆脱被弃用的命运。
参考资料:
1. 《清史稿·李卫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乾隆朝起居注》一书,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于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