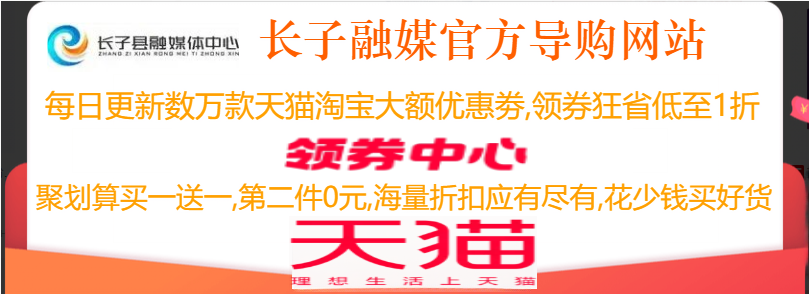从苏州归来,那粉墙黛瓦间蜿蜒曲折的小径依旧在我脑海中回荡。女儿向我推荐的童寯先生的著作《东南园墅》就放在案头,随手翻开,便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园林的神秘世界。这位被誉为“中国园林研究第一人”的民国时期学者,果然凭借其博学中西的深厚底蕴,将文字锤炼得如同精金美玉——常常只用一二十个字就能道出景观的精髓,其精辟之处如金石落地,字字珠玑,无不显现出文人的敏锐眼光。
近日网购的《苏州微旅行》还静静地躺在书架上,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实用的指南,但其文字却透露出一种“浅浅松松”的坦率,与此相比,竟觉得有些索然无味。此刻我忽然领悟到:只有用像东方园林一样精妙的笔触来描绘东方园林,才能达到“双美”的境界——文字与对象相互映衬,就像亭台与池水相互映衬,别有一番情趣。如今,每天翻阅《东南园墅》的一页,竟然成了回味苏州之旅的最佳方式。
网师园中的芭蕉,寥寥数语便揭示了其中的奥秘:“需透过窗户远观,方能显现其独特之美。”在游园之际,我曾瞥见过芭蕉的疏影,当时只将其视为普通的草木。然而,在童老的笔下重新追寻记忆,那片叶影竟然突然焕发出灵气——原来美是需要被点拨的,正如园林需要游客驻足沉思。这时,我突然想起,苏州不仅仅被称为“文化苏州”,更是“文人苏州”,是千百年间文人雅士的智慧与匠心,赋予了它永恒的生命力。
留园曲溪楼的阐释令人深受触动。童老提及,往昔园主多不在园中夜宿,而这“距离感”恰好使得园中景色成为心中难以忘怀的朱砂印记。“距离美”这五个字犹如醍醐灌顶,让我猛然想起常去的圆明园苹香榭——那片仅存基址的“残园”。它总能勾人心魄,或许正因为它像一面镜子,让人在断壁残垣间瞥见江南园林的幻影,这也更深刻地印证了童老的见解:真正的美,是无法被毁灭的。
童寯那一代文人,对汉字“惜墨如金”的内涵领悟得非常深刻,这原本是中国书写中体现高雅含蓄的特质。然而,近代翻译文学的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凝练之美。现在,有些文字往往过度“倾泻”,泥沙俱下,失去了应有的节制。或许,当代某些名家对于粗陋物象的偏爱,也与他们难以驾驭笔墨的浮躁心态有关。

环秀山庄假山图侧,童老仅以“我国古典园林,实乃立体画卷”六字题词。所谓“立体画卷”,深刻揭示了园林之精髓——它非平面绢画,而是一幅可身临其境的立体画卷。无论你身处何地,假山的皴纹、池水的空白、廊榭的题字都会随着脚步的移动而变化,宛如无数古画在天地间缓缓铺展。
网师园中的“真意”之门,其照片令人叹为观止。当日我曾在那里拍照录像,却未曾领悟其妙处。直至看到童老批注:“真意门洞,情趣的重要性远超技巧与方法。”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陶渊明的名句——“此中有真意”——技巧虽然易于掌握,但能洞察形制,洞察“真意”的慧眼,却是世间少有。留园中的那片斑驳铺地,初见时只觉得图案颇为特别,细细观察后才发现,竟然巧妙地融合了藕、莲、荷的生动意象,当年造园者的巧妙构思,不禁让人心生敬仰,不禁低首沉思。
拙政园中的“梧竹幽居”一区,童老提出了一个见解,他认为“风景园”并不等同于“风景绘画”,而是超越了后者。这一观点与“文艺源于生活”的理念相契合,但又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当你身处那烟雨蒙蒙的亭子之中,凝视着水波在竹影中荡漾,聆听雨滴敲击着青瓦的声响,这种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又岂是平面的画卷所能完全捕捉的呢?尽管书中的插图设计得非常精致,却无法捕捉到园林四季更迭所展现的生动气息,这或许正是“超越”的真正含义所在。
合上书本,窗外的月光恰到好处。童寯先生用文人的视角审视园林,用诗人的笔触描绘园林,最终使得文字与园林达到了“双美”的和谐统一。而那本《苏州微旅行》,虽然实用性较强,但韵味却略显不足——原来,要写园林就如同造园一般,笔触需留有山水的余地、花木的遮掩,才能让读者在文字间领略到层层递进的审美境界。在明日清晨的阳光下,不妨再次掀开书页,一睹童老如何运用文字,于纸张上堆叠山石、整理流水,重新构筑一座充满精神风貌的苏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