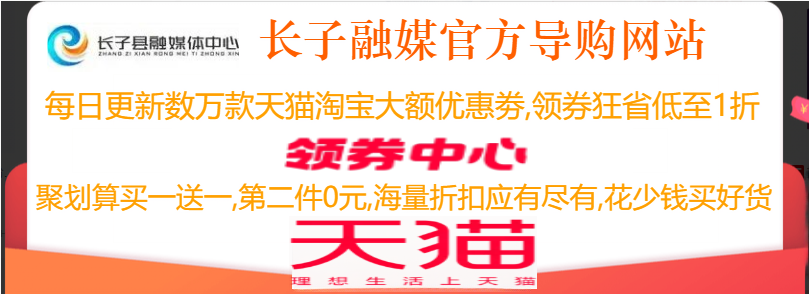自西方现代主义时期开始,绘画与美术艺术逐渐与自然分离,这导致在欣赏与解读方面,对于观众群体,尤其是我国观众而言,变得相当困难。
这里的“自然”蕴含着两层意义:一方面指的是感官所感知到的物理事实的固有属性,即那种眼见为实的写实风格的艺术;另一方面则是指审美情感的自然流露,例如那些笔触流畅、意境深远的中国传统写意画作。当然,这种风格的高接受度,主要在中国观众中产生共鸣。
西方的当代美术作品常常让人感到其形态怪异、风格抽象、内涵深奥,这些特点形成了人们接近和认同它的难点。即便在数字技术普及、国际艺术界充满活力的今天,仍有许多中国观众对现代主义美术缺乏鉴赏能力,这部分人中甚至包括了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
感性之缺乏审美教育无疑是关键因素,然而,感性审美的培养同样亟需理性思维的构筑。鉴于此,本文基于西方美术发展的实际轨迹,逐一剖析并提炼了一套观察、解读现代主义美术杰作的路径和策略。
现代主义美术的起点,在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在后印象主义时期,而塞尚则被誉为“现代绘画的奠基人”。塞尚的艺术生涯充满艰辛,即便是与他同行的、他本人也极为推崇的马奈,也对那些看似笨拙的作品不屑一顾。这充分表明,自现代主义诞生之初,便遭遇了广泛的误解和排斥。
马奈《草地上的午餐》
实际上,早在1863年,马奈便已创作出了诸如《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匹亚》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后来的印象主义运动中展现出了更为前卫的特性。与莫奈、雷诺阿等印象派画家专注于对写实艺术和实证主义哲学在“光色”领域的深化探索不同,马奈的作品刻意削弱了写实的基础,通过透视的偏差、平涂的绘画技巧,使得空间与造型呈现出明显的平面化趋势,其中已蕴含了现代艺术的倾向。
晚期的塞尚洞察了其中的精髓,他倾注了毕生心血,成功构筑了现代主义绘画的形态结构语言规范。他所创作的静物、风景、人物画作,其核心并非追求文学性的主题,更在于挑战传统写实艺术的真美感,以及印象派光影瞬间的视觉呈现。
塞尚《静物》
在欣赏塞尚的杰作《静物》、《圣维克多山》、《大浴女》和《自画像》时,我们无法领略到普桑与安格尔那写实与理想并存的精致造型,亦无法感受到莫奈、雷诺阿、德加、毕沙罗等大师们对色彩微妙变化的真实描绘。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一些略显扭曲、不够灵活的形体与色块的组合,以及空间感上的起伏变化。对于习惯了经典画作欣赏的观众来说,这样的体验自然难以称得上愉悦,尽管这些作品富有新意,但它们与我们的审美情趣似乎存在一定的隔阂。
英国形式主义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将塞尚的创新成果誉为“富有深意的形态”。自塞尚始,画面构图不再以复制现实物象为目标。塞尚的抱负在于,绘画从此不仅具有主观性,而且在主观表达中构筑了一套广泛适用的形式审美原则。我们观察到,他将苹果、山石、人体等元素,运用圆、圆柱、圆锥等几何形态进行加工,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使得它们在视觉上显得和谐相称。因此,画面在构图上展现出一种自由而均衡的稳固感。色彩的冷暖对比,不再像印象派画家那样严格遵循自然规律,而是在冷暖的规则中得到了自由的发挥。空间感则呈现出一种介于三维立体与二维平面之间的浮雕效果,同时,画家的笔触也显得随性而生动。后世的现代派画家们几乎无不从塞尚的思想中汲取灵感,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进而拓展。这种联系颇似柏拉图理念对现实世界的统治力,后者是前者纯粹存在的延伸。因此,塞尚得以成为现代审美领域的奠基人,一位全新的立法者。
在思想意识的根本层面,康德这位十八世纪的现代性哲学巨匠,与十九世纪的塞尚在精神上更为契合。他引领了哥白尼式的认识论变革,将知识的本质从主观与客观的契合转变为客观现象与主观先验认识的契合,从而确立了理性主体的普遍价值。这一转变与塞尚在视觉艺术中揭示的现代性感性审美原则,在本质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塞尚的画作问世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彼时欧洲社会正经历着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宗教关系的疏离,主体意识觉醒,并被迫转向人与自我、人与机械的全新精神交流。这一社会结构的变革,在思想领域可追溯至康德的理论,在科技领域则根植于工业革命,而在美学领域的开拓者正是塞尚。当然,这一变革背后的根本动力,源自资本主义的发展。
塞尚之后的诸多艺术派别,在表现形式上逐渐趋向主观化、意象化乃至抽象化。在这些艺术流派中,以形式主义美学特征著称的包括马蒂斯的野兽派、毕加索的立体派、康定斯基、马列维奇、蒙德里安的抽象绘画,还有二战后波洛克、德·库宁所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以及极简主义等。
形式构成了存在的基础逻辑,这一观点在柏拉图的“理式说”(亦称理念)以及亚里士多德对“形式因”的阐述中得以体现,它构成了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历史传统。在艺术领域,视觉形式往往拥有更为明确的权威地位,而题材与主题则往往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在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常常处于隐蔽不显的状态。通过直观美术作品的形式,我们便能把握其精神的核心。所以,在接触此类现代主义艺术作品时,我们应首先确立一种对新颖形式无保留接纳的审美视角,甚至将“丑陋”现象也纳入形式主义研究的范畴。
毕加索《亚维农少女》
1907年毕加索的《亚维农少女》虽不能激发(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普遍美感,却能有效激发人们对新颖视觉形式的感知,进而唤醒生物感官的感性潜能。蒙德里安的“抽象格子”艺术,以及马列维奇的《白上白》和罗斯科的“色域绘画”,可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现代主义审美风格,即抽象艺术达到极致的体现。在审视此类作品时,我们不如深入色彩与笔触的视觉传达,去探索其纯粹的形式构成,并尝试与之产生共鸣,无论是那种充满活力与宽广视野的审美,还是那种富有个性与叛逆精神的情感表达。
在众多受塞尚形式主义美学影响的艺术家中,马蒂斯特别强调个人情感的流露。尽管野兽派以“野兽”命名,却罕见地展现了一种优雅的品位,这在《红色的和谐》和《舞蹈》等作品中尤为突出。马蒂斯的画作极大地强调了平面空间的运用,以及主观色彩的鲜明对比,这既是对塞尚的继承,也是对其艺术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康定斯基,被誉为“抽象艺术之父”的另一位现代主义大师,以其充满音乐感的抒情风格闻名于世。他运用杂乱的点、线、面和色彩,构筑了一个充满情感的领域。在他看来,形式不仅是意志的体现,更是与情感紧密相连,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显然是对塞尚那种“编程式”的美学法则注入情感后的产物。最早尝试这一做法的是同样属于后印象主义画派的梵高,尽管与另一位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相比,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梵高也受到了塞尚的影响(甚至两人之间还有嫌隙),但在时间顺序上,梵高确实是在塞尚进行探索之后,将主观的形式转化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表达。当然,不能断言塞尚的表现手法全然冷漠无情,这样的评价并不公正。塞尚作品中那种节制而固执的形态,正是他情感的体现。然而,在塞尚的作品中,对纯粹结构性的探索显得尤为关键。随后,抒情画家梵高激发了另一个艺术流派的诞生,那就是德国的表现主义。以桥社为例,其精神领袖蒙克以及核心成员基希纳、罗特卢夫、赫克尔等人,他们倾向于运用粗犷、诡异的图像和笔触,来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压抑与痛苦。在这样的创作中,形式已不再单一,而是蕴含了丰富的内在精神特质和深刻的社会属性。
蒙克《呐喊》
与康德的主体哲学所强调的理性先验法则相比,在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体系中,意志被赋予了更为核心的角色。依据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思维逻辑,人们无法认知世界的本质和根源,但能够凭借自己的意志将其直接展现出来;而先验或后验的思想模式(即理性形态)也仅仅是意志发展过程中的残留痕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塞尚所倡导的形式美感原则在梵高、蒙克等艺术家的非传统思维中遭到了直接的破坏,他们的创作作品在生命力的展现上,相较于塞尚,更具有饱满的饱和度。
因此,现代主义美术的又一层内涵得以展现——即意志情感在表达过程中的符号象征价值。尽管这一点在梵高及其部分表现主义同仁的作品中并不突出,但仍有人对此进行解读。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画家多次描绘的“向日葵”这一图像符号,它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
这种对象征和寓意的清晰追求,最初在高更及其紧密相连的象征主义群体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以高更为例,他不仅继承了塞尚的形式主义,并融入了梵高式的个人情感,而且更加强调了图像作为符号所具有的意义特质,也正基于这一点,高更自称为“综合主义者”。成立于1886年的象征主义绘画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亨利·卢梭、夏凡纳、莫罗、雷东以及勃克林等人。这些人深受诗人马拉美、波德莱尔等人的启发,他们在作品中追求诗意和神秘感,精心构思图像,并强调主观感受和幻想世界对于精神层面的重大意义。
在美术领域的创作中,图像符号的意义表达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时期。那时,为了广泛传播基督教教义,美术作品并非以视觉真实或美感为价值所在,它们更多的是以图示和图解的形式存在。图像中的意义由教会预先设定并注入,形成了众人熟知的神学符号体系。例如,十字架代表着救赎,鸽子象征着圣灵,羊羔象征着信徒,金色代表着神性,衣褶则象征着运动。索绪尔这位语言学家把符号划分为感性的能指和概念性的所指两个层面。在中世纪的美术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对视觉符号所指的重视。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图像的能指层面经历了转变,从先前被有意忽视的生硬、平面的视觉效果,演变成了对立体写实性的深入研究。此时,充满真实感的空间成为了传达所指意义的人文主义审美的重要媒介。此外,在图像符号的指代范畴内,存在一种十七世纪崭露头角的“瓦尼塔斯”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以骷髅、腐烂的水果、沙漏等元素,寓意着生命的易逝与时间的流逝。这些元素均可视为西方美术史上“公共象征”阶段的艺术表现形式。

自高更之后进入象征主义时期,图像符号不仅在能指层面上受到了现代主义的视觉重塑,其符号所蕴含的意义规则亦在主观表达层面得到了重新定义。在欣赏高更晚年的杰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时,我们……在欣赏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仅被其独特的形式所吸引,而且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对作品中人物、动植物、神像之间关系的深入解读之中。同时,我们也会对亨利·卢梭在《狂欢节之夜》、《梦》、《热带森林》等作品中呈现的神秘而奇异场景产生浓厚的兴趣,不知不觉地开始“解读”这些画面……
高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局部)
所谓“象征”,即以某一事物或现象来隐喻另一事物或现象,唯有如此,方能更深刻、更具神奇性地触动心灵感知。在象征主义画家的普遍观念中,现实世界并不可信,唯有精神才是真正的存在。若要踏入那幻想与神秘的领域,象征手法便成为了通往灵性世界的狭径。这种强调主体性和主观性的认知与现代哲学的启示有着紧密的联系;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众多哲学巨匠,他们对于非理性、直觉、潜意识的优先地位予以高度评价,为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精神视野。此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象征主义艺术家群体亦深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理由在于,部分象征主义画家模仿科学研究的方式,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图景进行了细致的编码,仿佛一本心理分析的艺术指南,以此来更有效地引导观众深入理解。若此观点成立,不禁让人感叹,西方人对理性的执着确实是极为强烈的。
高更开启了象征主义的大门之后,一种将视觉符号转化为主观象征的艺术技巧,这种手法被蒙克、克里姆特、基里科、达利等众多艺术大师所采纳并进一步发展。他们引导观众踏入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艺术世界。当然,这些大师们的艺术语言都根植于个性化的形式创新之上。
观众在感性层面上对图像进行审美时,既能从解读图像所蕴含的意义中获得共鸣的喜悦,亦或是在图像含义模糊不清时,被其引发的神经刺激所吸引,感叹艺术的奇妙,这其中都蕴含着现代艺术的丰富智力趣味。
在现代艺术领域中,存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流派,其核心理念是全面抵制,不仅在社会领域内对一战持批判态度,对政治亦抱有反感,而且在艺术创作上更是走向了“反艺术”的极端。这一流派便是达达主义。
实际上,达达主义的大量作品并非全部都显现出明显的反艺术或非艺术特质,它们在形式和意义上与之前的众多流派相比,显得更加杂乱无章和偶然性更强;例如,苏黎世达达的重要成员汉斯·阿尔普以及毕卡比亚的作品,尽管具有前卫性,却依然保留了一定的现代绘画风格。
然而,1917年马塞尔·杜尚将那件知名的小便器《泉》置于展厅,达达主义反艺术的极端本质得以充分展现。《泉》被誉为现成品,即对日常物品稍作改动或直接赋予其“艺术品”的称号,此类艺术形式后来常被称作装置艺术。
马塞尔·杜尚《泉》
观众对于这类现成品的反感和荒谬感,与他们对早期现代主义美术在形态与色彩上的丑陋感受截然不同。艺术家只需挑选一件普通物品,签上自己的名字,将其移至展厅,它便即刻获得了艺术的至高地位。实际上,早在1913年,杜尚便已创作出了第一件现成品——那便是《自行车车轮》。在《泉》问世之后,杜尚继续拓展了他的艺术领域,创作了一系列充满恶搞精神的达达主义作品,其中不乏“蒙娜丽莎画小胡子”等颇具讽刺意味的杰作。
达达主义是现代美术思潮的一部分,然而杜尚的先锋行为却让他成为了连接后现代主义的纽带式人物。换言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后现代美术,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杜尚的启发。
此类作品的价值何在?这不仅是现代主义美术领域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构成了后现代及当代艺术领域的一大挑战。
马塞尔·杜尚《自行车车轮》
简单来说,就是观念。
这种理念并非是对知识与真理的直接传达,而是一种对现有认知方式的创造性逆转。艺术家或许并未对物品的形状进行实质性的改动,但他们通过调整物品或行为的“情境”——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将周围环境视为一个语言体系,这一观念源自西方的理性认知传统,即通过语言来重现世界——巧妙地运用了“四两拨千斤”的技巧,从而实现了作品的创作。
所有艺术门类并非仅仅是已知信息的阐述,若如此,它们便沦为了学术论文。艺术的本质在于激发并展现那些未知领域,旨在唤醒那些超越或独立于确定理性之感觉,这一点在诗歌、戏剧、音乐、美术反复创造出令人惊喜的精彩瞬间中,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观念艺术将战场转移至“纯粹认知”的领域,运用反视觉、非审美的独特手法,通过错位、矛盾等形式的“棒喝”,对艺术、生活的基础理念进行了颠覆,进而实现了其艺术价值。在这些手法中,最常采用的是对物品、行为存在“语境”的转换。
这类观念艺术的内在理念,与维特根斯坦在后期所提出的语言哲学,还有解构主义哲学的诸多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维特根斯坦以及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等人的后期著作中,他们都对那个明确的“符号-概念”认知体系提出了疑问,并认为符号及其所承载的意义,实际上是在感知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偏移、生成、误解以及变化的。古典时代以来构建的符号规则,实则都只是以文明为名的理性霸权。文明的发展,旨在打破权威的束缚,将语言的意义回归到一系列复杂的关系之中。此外,还需主动创造更多错位和误读,以此维持社会的活力,并朝着更加开放的可能性不断拓展。
人类天生渴望寻求确定性,这与贪念与恐惧相似,然而在当代后现代主义视角中,“确定”被视为一种权力和惰性。此类艺术形式亦被与中国禅宗思想相类比,禅宗的挑战权威、不拘泥于文字、瞬间领悟空性的理念,确实吸引了众多西方艺术家,其中最为知名的有约翰·凯奇、克莱因、波洛克等人。并无确切证据证明杜尚曾受到禅宗的启迪,若二者观点相似,那不过是智慧的偶然交汇。
对现代主义美术发展的这一梳理依照的是线性思维,但在实际情境中,情形往往更为繁杂,具体到个别作品时,其界限也未必清晰可见。
艺术并非纯粹基于理性的科学探究,亦非超越经验的宗教崇拜。尽管西方艺术常以科学作为其技术根基,且艺术家们往往向往宗教并从中汲取灵感——但若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艺术家们常常将难以捉摸的超验信仰、超越感官的戒律,与动物的直观感受相混杂,以此来满足艺术创作中对欲望和灵感的追求——然而,艺术本质上仍旧是艺术。
理清底层逻辑虽然不能直接培养出伟大的艺术家,但确实能极大地促进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观赏与理解,就好比建筑过程中搭建的脚手架。正因如此,我把现代主义艺术概括为三个层次:首先,重视视觉表达层面的“形式”;其次,关注内涵表达层面的“象征”;最后,注重社会文本关系层面的“语境”。在这其中,前两个代表了典型的现代主义脉络,而第三个则与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代艺术的脉络相衔接。
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起在社会领域,其根源可追溯至工业文明的进步,这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文主义创新精神走向极端的显著标志。这一进程始于对普遍性、大写的“人”的强调,随后逐渐转向对个体差异的重视,并将这种个体意识通过英雄主义的手法进行了放大——梵高、高更、毕加索等艺术巨匠,正是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是被迫启动的,在我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中,个人主义和追求“新颖”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尽管诸如徐渭、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个性发展的特点,但他们的意识和趋势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
历史对“个人”而言,偶然性胜过必然性,感性成分多于理性。众多艺术家,乃至那些推动历史进程的人,在创作过程中,往往遵循着一套与常理不同的个人欲望逻辑。我们对于这些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往往依赖于后世基于自身需求所做的总结。这也揭示了上帝或历史的逻辑与个人生命追求的逻辑之间始终存在的差异,上帝或历史的长者必须挑选一位天才来引领某个线索的进展,而这名天才仅仅是凭借自身的生命力量去实施,其动机往往并非后世所归纳出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有意识行为。这体现了现实的巧妙,也蕴含着命运的奥秘。
作为审视现代艺术史乃至所有历史的我们,需对历史的演进层次、创作者的创作初衷,以及观赏者个人的独特感受,进行一次全面的融合。只有这样,观赏才能变得有趣,才能与创作并驾齐驱,成为一门卓越的学问。(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