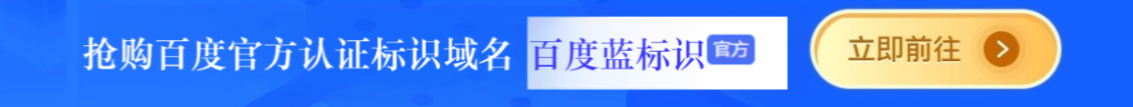OpenAI自从去年11月那场内部纷争之后,正遭遇着自那时起最为严重的内部挑战。
2025年6月底,该AI行业巨头不仅遭受了来自Meta的“人才抢夺战”——在短短一周内,至少有7名关键研究员被挖角,而且不得不宣布自公司成立以来首次的“暂停运营”:在6月30日至7月6日这段时间里,员工们被要求实行居家办公,而管理层则不得不加班加点,全力应对这场人才流失的危机。
此次事件不仅凸显了OpenAI内部长期存在的管理弊病,而且进一步表明,随着AI行业竞争日趋激烈,顶尖人才已经变得比计算能力更为珍贵,成为了争夺的焦点战略资源。
Meta向一位研究员提供了高达一亿美元的丰厚签约奖金,与此同时,OpenAI的首席研究官Mark Chen将这种挖角行为比作有人擅自闯入自家家中窃取财物。
这场围绕人工智能领域顶尖大脑的竞争,已经彻底重塑了硅谷的人才竞争格局。
OpenAI内忧外患
2025年6月28日,OpenAI的首席研究官Mark Chen向全体员工散发的强硬备忘录,宛如一颗沉入水底的炸弹,将公司内部长期积压的矛盾暴露于众。
我们前所未有的积极,正在对薪酬体系进行优化调整,同时积极探索新的途径,以表彰并激励那些卓越的顶尖人才。
这封邮件是对Meta近期频繁吸纳OpenAI多位关键研究员行为的直接反击——根据公开资料,至少有7位在GPT-4o、o系列模型研发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杰出人才已加入Meta,其中不乏多位具有华裔背景的科学家。
OpenAI采取的应对策略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不仅承诺对薪酬体系进行改进,而且宣布从6月30日至7月6日,全体员工将暂停工作整整一周。
Mark Chen与山姆·奥尔特曼
名义上是为了减轻员工每周承受的超过80小时工作时间的压力,然而,据知情者透露,管理层的真正意图是阻止关于离职的传闻在办公场所扩散,以避免引发更广泛的员工情绪波动。
在硅谷,这种所谓的“鸵鸟策略”并不少见——比如,Meta在之前进行裁员时就曾运用过类似的方法——然而,对于以技术革新著称的OpenAI来说,这却是一种全新的危机应对手段,充分暴露出其管理层所面临的焦虑已经达到了极限。
人才短缺的隐患自2024年起便已埋下根基。伴随着OpenAI由一所以研究为主体的机构向商业化企业的转变,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
以山姆·奥尔特曼CEO为首的团队,力主加速产品更新和盈利进程。
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沃及其所代表的团队,他们主张在研发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过程中,伦理风险应当被置于首位,给予优先考虑。
伊利亚·苏茨克沃(Ilya Sutskever)
2024年8月至9月,苏茨克沃、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以及CTO米拉·穆拉蒂等资深成员纷纷选择离职或休假。进入2025年,OpenAI最初的11位创始人中,仅有3人坚守岗位。与此同时,接替离职高管的新任者,大多是奥尔特曼所信赖的具备商业化能力的专业人士。
战略的摇摆不定与领导层的缺失,导致OpenAI在技术上的纯粹性逐渐减弱。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奥尔特曼提出“每隔数月必须推出重量级产品”的要求,这使得研究人员不得不忙于追逐短期目标。
John Schulman,这位曾主导GPT项目开发的负责人,在离职之际坦诚表示,他渴望“回归到具体的技术岗位”——这种含蓄的批评实际上揭示了OpenAI逐渐显现的官僚主义问题。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在Mark Chen的备忘录中,他着重指出“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追求核心目标——研究如何将计算力转化为智能”,然而,这一表述实际上是对OpenAI过去一年多以来商业化策略的一种质疑。这种自我矛盾的行为,恰恰暴露了公司战略上的混乱。
薪酬结构的不合理问题进一步导致了人才的大量流失。尽管OpenAI的市值已经达到了1500亿美元的惊人数字,然而其特有的“利润封顶”机制却对员工的收益产生了限制——起初,公司向投资者承诺的回报不会超过投资额的100倍,随后这一承诺调整为每年的收益增长20%,这表明在理论上,40年后利润的极限可能达到100万亿美元。
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OpenAI在薪酬上难以与Meta等竞争对手的高额报价相抗衡。当奥尔特曼在播客中公开Meta提供的“一亿美元签约奖金以及更高的年薪”时,他可能未曾料到,这样的言论竟然促使众多员工开始深思自身的市场价值。
OpenAI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揭示了其非营利宗旨与商业运作之间的矛盾。自2019年起,公司设立营利性子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大规模融资,然而在微软投入130亿美元之后,公司逐渐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既要满足投资人的回报要求,又要确保安全地开发通用人工智能,这两个目标似乎难以同时实现。
2024年启动的重组计划,涉及将核心业务移交至一家营利性企业进行运营,而非营利性质的董事会仅保留少量股份。这一举措使得公司全面转向商业化,进而直接引发了安全派高管的集体离职。
如今,Meta以重金揽获技术精英,而OpenAI这才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理想主义的荣耀,而且未能构建起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架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Meta的"复仇式挖角"
2025年6月中旬,Meta公司对数据标注企业Scale AI的巨额投资达到了143亿美元,这一举动在硅谷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这笔交易不仅使Meta成功收购了Scale AI 49%的股份,而且还将年仅28岁的创始人Alexandr Wang纳入旗下,并赋予他“首席人工智能官”的重要职位。
人们未曾预料到,这仅仅是扎克伯格AI布局的开端;两周之后,Meta公司宣布设立了“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MSL),将FAIR研究团队、Llama模型开发组等AI相关资源进行了整合,并由Wang全面掌管;而这个实验室的核心成员,则主要是从OpenAI那里吸纳而来的优秀人才。
扎克伯格亲自指挥,使得此次招募活动效率极高。据知情人士透露,Meta的首席执行官不仅亲自编制了一份全球顶尖AI研究人员的名单,而且还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和太浩湖的家中与候选人进行了面谈,甚至为关键人才特别设立了无需面试的“快速通道”。
CEO直接招聘的模式显著缩短了决策流程——从初次接触直至正式签订合同,有些案例只需72小时即可走完所有步骤。这种迅速果断的工作风格与OpenAI的官僚作风形成了强烈反差,对于长久以来饱受繁琐程序困扰的研究人员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Meta的招募策略并非仅仅是依靠金钱的诱惑,而是对OpenAI的核心技术进行了精确的打击。在这11位被挖走的人才中,有7位原本属于OpenAI,他们主要分布在多模态模型、语音交互、强化学习等至关重要的领域。
毕树超,作为GPT-4o语音模式的关键构建者,扮演着核心角色。
于佳慧,这位杰出的研究者,担任了GPT-4o图像生成系统的核心项目负责人。

赵晟佳(Shengjia Zhao)担任OpenAI合成数据团队的负责人,他参与了从GPT到GPT-4o这一系列重要项目的全过程。
这些人才的集体离职,不仅将导致OpenAI o系列轻量模型的更新速度受到阻碍,而且极有可能打断其多模态技术的持续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Meta公司实施的人才争夺策略早已露出端倪。在2025年的开端,其自主研发的大规模语言模型Llama 4的表现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被国内企业DeepSeek等竞争对手所超越。
知情人士透露,扎克伯格对此感到极度失望,于是迅速对AI的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他决定不再仅仅依赖单一模型,而是通过招募业界精英,力求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
这种策略与学术界所谈论的“明星教授”现象有着相似之处;MIT机械工程系主任陈钢曾指出,顶尖高等学府的成就关键在于“预测哪个领域将迎来重大突破,并寻觅那些有潜力实现这一突破的人才”。而Meta公司目前正在实行的,便是将这一策略成功应用于企业研发领域。
薪酬的吸引力固然明显,但更深层次的吸引力则源于科研的自主权和充足的资源支持。Meta向MSL团队承诺将提供“不受限制的顶级计算资源”,这对于一直受制于GPU短缺的OpenAI研究人员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诱惑。
知情人士透露,与OpenAI关系密切,该公司内部经常围绕算力分配问题引发激烈的争论;一些关键项目尚需排队等候资源,而边缘性研究则更难以获得支持。扎克伯格宣布未来数年将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数千亿美元,展现出了all-in的决心。与此同时,OpenAI在AGI研发方面却显得犹豫不决,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抱有理想的研究者来说,这种对技术的信仰或许比金钱更具吸引力。
山姆·奥尔特曼 × 扎克伯格
Meta的招募行为同样揭示了硅谷人才流动的体制背景。根据加州法律,竞业禁止条款被明令禁止(《加州商业和职业法典》第16600条),因此科技公司几乎无法阻挡员工跳槽至其他竞争对手那里。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AI研究领域内,存在着一种显著的“师承现象”——在此次被挖角的OpenAI研究员群体中,许多人拥有谷歌DeepMind或斯坦福大学的学术背景,从而构筑起了一个紧密相连的学术家族网络。这种基于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的信任纽带,其稳固性远超于对公司的忠诚度,一旦有成员成功离职,往往会导致整个小团队集体流动。
面对外界对于“1亿美元高额合同”的诸多疑问,Meta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安德鲁·博斯沃思给出了颇具深意的回答:“萨姆(奥尔特曼)并非诚信之人……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获得如此巨额的报酬。”
Levels.fyi的统计表明,Meta公司中E7至E9级别的工程师年薪大致介于150万至500万美元之间,然而为了争夺人才,他们可能愿意支付高达原薪1.5倍的额外费用。独立分析师推测,那些被挖角至OpenAI的研究员,其整体薪酬大约在500万至1000万美元每年,虽然这个数字并没有传言中的那么夸张,但与OpenAI现有的薪酬水平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这种“新人欢笑旧人泪”的现象甚至激起了Meta内部的怨声载道,资深员工纷纷抱怨公司以2至3倍的薪酬吸引外部“超级巨星”,此举无形中削弱了现有团队的价值。
扎克伯格发起的这一人才争夺战,其核心在于对Meta技术战略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借助OpenAI旗下人才的加入,Meta意图填补自身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不足;同时,Scale AI的数据标注实力与Wang所带领的算法团队相结合,有望催生出与GPT截然不同的技术发展方向。
这种所谓的“杂交优势”能否真正超越OpenAI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然而在短期内,它已经有效地扰乱了对手的研发步伐,实现了多方面的收获。正如剑桥大学的计算机教授乔恩·克洛克夫特所说:“在创新周期中,人工智能人才的激烈竞争本是常态”——然而,这次Meta却让这个“常态”变得异常残酷。
AI人才争夺加剧
在OpenAI与Meta为争夺个别研究人员而激烈竞争之际,一个更为广泛的趋势逐渐浮出水面: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正步入“人才短缺”的新阶段。
麦肯锡的最新预测指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在AI领域将面临高达400万的缺口。与此同时,美国顶尖AI研究者的培养费用已经超过了每人200万美元。这种供需的不平衡导致了市场结构的扭曲,形成了所谓的“卖方市场”。以2025年春季招聘为例,算法工程师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了46.8%,平均月薪达到了2.35万元人民币,而深度学习岗位的月薪更是高达2.4万元。
在中国,诸如宇树科技等初创企业,对于AI算法岗位的薪资待遇高达每月7万元;而广东神舞科技更是慷慨至极,为算法工程师提供"两室一厅的免费住房"以及"年薪在40万至70万之间"的丰厚。
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导致行业内部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制度”。据科技领域的猎头人士透露,OpenAI、Anthropic以及谷歌的DeepMind位居金字塔之巅,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学术影响力,能够吸引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人才;马斯克的xAI因其激进的技术理念而迅速崛起;而Meta则因Llama 4项目的失利而略逊一筹。亚马逊、苹果和微软等第二梯队的公司,常常以“股权变现”作为吸引人才的亮点;而Perplexity、Cohere等独角兽企业,则主要凭借创业热情和灵活的管理机制来参与市场竞争。这种层级划分造就了显著的马太效应——上游企业轻易地从下游企业挖走人才,而人才逆向流动则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AI人才的评定准则正迎来一场颠覆性的变革。以往以工龄和职称为基础的评价体系,正逐步被“AI年龄”这一新概念所取代。一个自12岁起便开始运用大型模型进行编程的中学生,在22岁毕业时,其“AI年龄”已达10年,其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或许已超越那些拥有20年传统编程经验,但“AI年龄”仅有2年的资深工程师。
这种变革正在对劳动力市场的价值观念产生根本性的转变——比如,28岁的Scale AI的创始人Alexandr Wang能够领导Meta公司价值千亿的AI实验室,与此同时,一些经验丰富的软件工程师却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在未来的职场竞争中,将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开发者与AI系统协同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将成为关键因素。
企业间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推高了顶尖人才的身价。微软向其AI团队支付了是其他部门两倍的薪酬,并且开出高达5万美元的即时奖金,强烈要求应聘者“立即中止所有其他面试”;谷歌DeepMind甚至动用了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亲自出面游说候选人;此外,据The Information披露,为了防止Meta公司挖角,OpenAI迅速批准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留任奖金。
这种激烈的竞标使得初级AI工程师的起始薪资已高达10至12万美元,外加15万美元的股权激励(分四年逐步实现),这几乎等同于资深传统软件工程师三到五年的薪酬水平。在扎克伯格为OpenAI的研究员提供高达千万美元年薪之际,他不仅锁定了竞争对手的研发实力,而且还彻底重塑了整个行业的薪酬基准。
这场人才竞争的深层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技术模式的变革。当大型模型步入“摩尔定律”之后的时代,仅仅通过扩大参数数量所带来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创新活动愈发依赖于算法的突破和工程上的优化——而这些均高度依赖于人类的智慧。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王亮研究员强调,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具备坚实基础研究和应用综合能力的人才,不仅要着力提升高端AI芯片的国产化水平和算法的原创性,还必须加快AI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推广。这种对“双管齐下”人才的需求,使得那些既精通理论又擅长解决实际问题的全栈型人才变得尤为珍贵。
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深,导致人才短缺问题愈发严重。尽管全球范围内超过五百所高等院校设立了人工智能相关课程,然而,大多数院校依旧沿袭着传统的计算机课程体系,培养出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
在江苏省某所“双一流”大学2024届AI专业毕业生群体中,竟无一人选择投身于相关企业工作,这一现象凸显了当前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的严重脱节问题。根据猎聘网的数据,目前从事AI行业的从业者中,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传统学科背景的人占据了较大比例。尽管他们在算法优化、系统架构等特定领域可能表现出色,然而,他们普遍缺乏跨学科的综合整合能力,这使得他们在面对“AI+行业”这种复合型需求时,往往难以胜任。
这场人才争夺战的最终结果,或许将引发全球人工智能力量的重新分布。值得注意的是,在Meta公司挖走的OpenAI研究员中,华裔的比例尤为突出。根据《2023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中,有47%来自我国,而在美国,顶尖AI人才中,华人的比例更是高达75%。
这种人才分布状况导致中美两国在AI领域的竞争呈现出一种奇特的“你中有我”的局面——我国培养的顶尖人才正在引领美国企业的创新突破,而这些人才所创造的技术又通过开源平台或商业产品回流至我国市场竞争。这种类似于“量子纠缠”的关系,将使得任何试图断绝联系的尝试都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面前,OpenAI和Meta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技术理念。Meta采取“以金钱换时间”的策略,通过高额薪酬迅速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而OpenAI则致力于回归“使命导向”,强调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愿景的纯洁性。
这两种方法究竟哪个更胜一筹,目前尚无明确结论;即便学术界不惜重金聘请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无法确保未来能够取得显著突破。Meta必须注意,一旦“雇佣兵文化”削弱了对技术的信仰,即便是阵容豪华的个体也可能变成一盘散沙;同时,如果OpenAI无法将AGI的理想变为现实中的科研环境与合理的回报,很可能会重蹈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的覆辙——那就是虽然孕育了革命性的思想,却未能留住那些创造这些思想的人才。
在这场无硝烟的较量中,真正笑到最后的人或许会是那些拥有“AI原生思维”的年轻群体。伴随着南开大学“人工智能赋能人才培养行动计划”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孩子从12岁起便开始接触大型模型,成为了“AI原住民”。他们与AI共同进化的“数字直觉”,或许比任何高额的薪酬都要更具革命性。在扎克伯格与奥尔特曼激烈争夺现有人才之际,我们或许更应深思:如何培育并挽留那些尚未被列入名单,却注定要塑造AI未来的“未来之星”。
终究,在人工智能领域这场指数级演进的赛道上,今日的杰出研究者或许在明日就会被算法所淘汰,然而,持久的竞争优势,始终源自于不断滋养创新人才的生态环境。